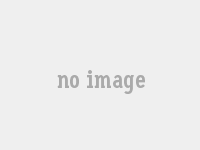不要輕易向孩子借運(yùn):你借一次,孩子的人生就會(huì)越來越差
晚飯后,電視機(jī)的音量被調(diào)到35,一個(gè)我媽耳朵剛好能聽清,又不會(huì)吵到鄰居的刻度。這個(gè)數(shù)字像一道無形的指令,宣告著家庭夜晚的正式開始,也圈定了我們所有人必須遵守的秩序。我放下碗筷,女兒萱萱正拿著勺子,笨拙地往嘴里扒拉最后一粒米飯。
我瞥了一眼客廳墻角的儲(chǔ)物柜,柜門有一絲不易察uc察的縫隙。我知道,那里面第三個(gè)抽屜,放著一本舊相冊(cè),相冊(cè)里夾著一張我五歲時(shí)的黑白照片,扎著兩個(gè)羊角辮,笑得沒心沒肺。那張照片,是我媽的寶貝,也是我心里的一個(gè)坐標(biāo),提醒我曾經(jīng)那樣被毫無保留地愛過。
“薈薈,碗放著,我來洗。”我媽的聲音從廚房傳來,帶著慣常的溫和。
我應(yīng)了一聲,卻沒有動(dòng)。今天的沉默格外漫長(zhǎng),從我進(jìn)門開始,她就有些反常。往常她總有說不完的話,從菜價(jià)漲了幾毛,到鄰居家兒媳婦又買了什么新衣服。今天,她只是默默地做飯,吃飯時(shí)眼神幾次飄向萱萱,帶著一種我讀不懂的復(fù)雜情緒。
丈夫周誠(chéng)加班,家里只有我們母女三人。萱萱吃完飯,吵著要看動(dòng)畫片,我媽難得地沒有依著她,只是摸著她的頭,輕聲說:“萱萱乖,今天奶奶有點(diǎn)累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我媽是個(gè)精力旺盛的人,累這個(gè)字,很少?gòu)乃炖镎f出來。
我把萱萱哄回房間玩積木,然后走進(jìn)廚房。我媽正背對(duì)著我,慢慢地刷著碗,水流聲嘩嘩作響。
“媽,你不舒服?”我問。
她關(guān)掉水龍頭,用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手,轉(zhuǎn)過身來。昏黃的燈光下,我看到她眼角的皺紋似乎又深了些。
“沒事,”她搖搖頭,嘴唇動(dòng)了動(dòng),似乎想說什么,最終又咽了回去,“就是……小薈,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,是關(guān)于萱萱的……”
“萱萱怎么了?”我的心立刻提了起來。
“你別緊張,”她拉著我走到客廳的沙發(fā)上坐下,雙手交疊著,不停地揉搓著,這是她緊張時(shí)的標(biāo)志性動(dòng)作,“不是孩子身體不好。是……是她的名字。”
“名字?”我一頭霧水,“周梓萱,這名字不好聽嗎?當(dāng)初還是您和我爸翻著字典,一個(gè)一個(gè)字挑出來的。”
我媽嘆了口氣,聲音壓得更低了,仿佛怕被誰聽見。“好聽是好聽,就是……太大了。”
“大?什么意思?”
“前幾天我去給你弟求神拜佛,你知道的,他那工作一直不上不下,都快三十了,房子還沒個(gè)影兒。我就找了個(gè)很有名的先生問問家里的運(yùn)勢(shì)。”她頓了頓,觀察著我的臉色,“那先生說,我們家不是沒有好運(yùn),是被壓住了。”
我的眉頭皺了起來,一股不祥的預(yù)感涌上心頭。
“先生說,萱萱這孩子的命格好,名字也好,‘梓’是木中之王,‘萱’是忘憂之草,太大,太滿了。她一個(gè)小孩子,鎮(zhèn)不住這么大的名字,反而把家里其他人的運(yùn)道都給吸走了。尤其是你弟,首當(dāng)其沖。”
我簡(jiǎn)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媽,這都什么年代了,您還信這個(gè)?”
“你別不信!”我媽的聲音陡然拔高,但立刻又壓了下去,警惕地看了一眼萱萱的房間,“那先生算得可準(zhǔn)了。他說我們家去年破了財(cái),是不是?你爸那次炒股,虧了三萬多!他還說,你弟今年有個(gè)坎,過不去就要倒大霉!”
我感到一陣荒謬,又有些無力。“媽,炒股有賺有賠,這跟萱萱的名字有什么關(guān)系?我弟工作不順心,那是他自己能力問題,跟一個(gè)五歲孩子又有什么關(guān)系?”
“怎么沒關(guān)系!”我媽的眼圈紅了,“先生說了,只要把萱萱的名字改一改,改成一個(gè)普通點(diǎn)的,簡(jiǎn)單點(diǎn)的,把這好運(yùn)給‘讓’出來一點(diǎn),你弟的坎就能過去,家里的財(cái)運(yùn)也能好起來。”
我站起身,胸口堵得厲害。“媽,這太荒唐了!我不同意!萱萱的名字,一個(gè)字都不能改!”
“我不是在命令你,我是在跟你商量!”她也站了起來,拉住我的胳膊,聲音里帶上了哭腔,“薈薈,媽求你了!就當(dāng)是為了你弟,為了這個(gè)家!先生都給想好新名字了,叫‘麗’,美麗的麗,簡(jiǎn)單好記,又不會(huì)沖撞了家里的運(yùn)勢(shì)。”
周麗?
我腦子里嗡的一聲。我仿佛看到我那個(gè)靈動(dòng)可愛的女兒,被人硬生生奪走了屬于她的符號(hào),換上了一個(gè)平庸、普通、甚至有些土氣的代號(hào)。
“不行。”我甩開她的手,語氣前所未有的堅(jiān)定,“絕對(duì)不行。”
我媽愣住了,她沒想到一向順從的我,會(huì)拒絕得如此干脆。她看著我,眼神從懇求,慢慢變得失望,最后化為一絲冷漠。
客廳里,電視機(jī)還在兀自響著,音量35,那個(gè)熟悉的刻度,此刻卻像一把標(biāo)尺,精準(zhǔn)地量出了我們母女之間裂痕的深度。我知道,這個(gè)夜晚,只是一個(gè)開始。一場(chǎng)以愛為名的掠奪,已經(jīng)悄無聲息地拉開了序幕。
第一章
接下來的幾天,家里籠罩在一種詭異的低氣壓中。我媽不再提改名的事,但那件事就像一根刺,扎在我們母女心間。她對(duì)我依舊溫和,只是那溫和里,添了一層客氣和疏離。她不再主動(dòng)抱萱萱,只是在萱萱沖她撒嬌時(shí),才勉強(qiáng)地笑一笑,那笑容僵硬得像一張面具。
周誠(chéng)回來后,我把這件事當(dāng)成一個(gè)荒誕的笑話講給他聽。他果然笑了,大手一揮:“別理她,老太太就是閑的。什么年代了,還搞封建迷信。咱們女兒叫周梓萱,天王老子來了也叫周梓萱。”
他的不以為然讓我稍稍安心,但心底深處那份不安,卻并未消散。我太了解我媽了,她認(rèn)定的事,九頭牛都拉不回來。她的沉默,不是放棄,而是蓄力。
果然,周末家庭聚餐,戰(zhàn)火重燃。
飯桌上,我爸,一個(gè)平日里沉默寡言、存在感極低的男人,清了清嗓子,開了口。他從不參與家里的長(zhǎng)短里短,他一開口,必定是大事。
“小薈,你媽跟你說的事,你考慮得怎么樣了?”他一邊說,一邊用指關(guān)節(jié)有節(jié)奏地敲擊著桌面,篤,篤,篤,像在敲打我的神經(jīng)。
我弟林浩埋頭吃飯,假裝事不關(guān)己,但他豎起的耳朵出賣了他。
我放下筷子,看著我爸:“爸,這件事沒什么好考慮的。萱萱的名字,不會(huì)改。”
“胡鬧!”我爸的臉沉了下來,“這不是小事!關(guān)系到你弟弟的前途,關(guān)系到我們整個(gè)家!”
“一個(gè)名字而已,怎么就關(guān)系到整個(gè)家了?”周誠(chéng)忍不住插話,他臉上還帶著笑,但笑意不及眼底,“爸,這事兒不科學(xué)。”
“科學(xué)?科學(xué)能讓你弟立馬買上房、找到好工作嗎?”我爸的矛頭立刻轉(zhuǎn)向了周誠(chéng),“周誠(chéng),我們家薈薈嫁給你,我們沒圖你什么。現(xiàn)在家里有難處,需要你們幫一把,你們就這個(gè)態(tài)度?”
這話就嚴(yán)重了。我趕緊打圓場(chǎng):“爸,不是我們不幫忙。改名字這事太離譜了。阿浩的工作,我們可以幫他想辦法,錢不夠,我們也可以支援一點(diǎn),但不能拿孩子的事開玩笑。”
“誰跟你開玩笑了?”我媽的聲音尖銳起來,“我們是萱萱的親外公外婆,我們會(huì)害她嗎?不過是改個(gè)名字,又不是要她的命!你們?cè)趺淳瓦@么自私,只顧著自己那個(gè)小家!”
“媽,你怎么能這么說?”我氣得渾身發(fā)抖。
“難道不是嗎?你弟弟是你唯一的親弟弟!他過得不好,你這個(gè)當(dāng)姐姐的臉上就有光了?我們老兩口就指望他了,他要是垮了,我們活著還有什么意思?”她說著,眼淚就下來了,開始一下下地捶打自己的胸口,“我這是造了什么孽啊,養(yǎng)出你們這么一對(duì)自私自利的白眼狼!”
林浩終于抬起頭,怯生生地說:“姐,姐夫,要不……就算了吧。我的事,我自己想辦法。”
他這話不說還好,一說更是火上澆油。
我媽立刻把炮火對(duì)準(zhǔn)了他:“你閉嘴!沒出息的東西!你但凡有點(diǎn)能耐,我們用得著去求你姐嗎?指望你自己,黃花菜都涼了!”
“夠了!”我爸猛地一拍桌子,碗碟發(fā)出刺耳的碰撞聲。
整個(gè)餐廳瞬間安靜下來。
我爸的目光如刀,直直地射向我:“林薈,我今天就把話放這兒。這個(gè)名字,你改也得改,不改也得改。你要是還認(rèn)我這個(gè)爸,認(rèn)這個(gè)家,你就去辦。不然,以后我們林家,就沒你這個(gè)女兒!”
我徹底愣住了。斷絕關(guān)系?為了一個(gè)虛無縹緲的“運(yùn)勢(shì)”,為了給我弟“借運(yùn)”,我爸竟然要跟我斷絕關(guān)系?
周誠(chéng)的臉也冷了下來,他拉起我的手:“薈薈,我們走。”
“站住!”我爸吼道,“今天這事不說清楚,誰也別想走!”
氣氛劍拔弩張,餐廳里的空氣仿佛都凝固了。就在這時(shí),一直被我們忽略的萱萱,突然怯生生地開口了。
她仰著小臉,看看我,又看看外婆,小聲問:“媽媽,外婆是不是不喜歡‘周梓萱’了?”
孩子清脆的聲音,像一把錐子,狠狠刺進(jìn)我的心臟。
我蹲下身,把她緊緊摟在懷里,鼻頭一酸,喉嚨瞬間發(fā)緊。我強(qiáng)忍著淚水,柔聲對(duì)她說:“沒有,寶貝。外婆最喜歡萱萱了。媽媽也喜歡,爸爸也喜歡,我們都最最喜歡周梓萱。”
我一邊說,一邊抬頭看向我媽。她的身體僵住了,臉上的憤怒和激動(dòng)褪去,取而代之的是一絲慌亂和狼狽。她不敢看萱萱的眼睛,別過了臉去。
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了。他們不是不愛萱萱,只是在他們心里,那份愛被更強(qiáng)烈的焦慮和對(duì)兒子的偏愛給覆蓋了。為了安撫自己的焦慮,為了給兒子的未來鋪路,他們不惜從最柔軟、最不會(huì)反抗的外孫女身上,挖走一塊他們認(rèn)為可以轉(zhuǎn)運(yùn)的“肉”。
有些愛,就像冬天的棉襖,不穿冷,穿上,又喘不過氣。
我抱著萱萱,感覺懷里的小身體溫?zé)岫彳洝_@是我的女兒,是我生命的延續(xù),是我要用盡全力去守護(hù)的人。
我站起身,平靜地看著我爸媽:“爸,媽。錢,我們可以想辦法。工作,我們也可以托關(guān)系。但是萱萱的名字,就是她的底線,也是我的底線。你們要是真的為了這個(gè),不認(rèn)我這個(gè)女兒,那我也……無話可說。”
說完,我牽著萱萱,和周誠(chéng)一起,頭也不回地走出了那個(gè)讓我感到窒息的家。
門在身后關(guān)上,隔絕了父母的怒吼和哭罵。我走在小區(qū)的林蔭道上,晚風(fēng)吹來,臉上冰涼一片。我抬手一摸,才發(fā)現(xiàn)自己早已淚流滿面。
第二章
冷戰(zhàn)開始了。
我媽沒有再給我打過一個(gè)電話,我發(fā)過去的消息也石沉大海。我知道,我爸那句“斷絕關(guān)系”不是氣話,他們是來真的了。
周誠(chéng)看我情緒低落,想方設(shè)法地開解我。他會(huì)提前下班,買我最愛吃的蛋糕,或者在周末提議帶我和萱萱去郊野公園。他越是這樣,我心里就越是愧疚。這是我的原生家庭帶來的麻煩,卻讓他和孩子跟著一起承受。
一天晚上,萱萱睡后,我坐在書房的電腦前,心煩意亂地刷著網(wǎng)頁。周誠(chéng)走進(jìn)來,遞給我一杯熱牛奶。
“還在想那事?”他問。
我點(diǎn)點(diǎn)頭,嘆了口氣:“我就是想不通,我媽怎么會(huì)變成這樣。她以前不是這樣的。”
“人都是會(huì)變的,被生活逼的。”周誠(chéng)在我身邊坐下,“他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弟身上,你弟不爭(zhēng)氣,他們就慌了,病急亂投醫(yī)。”
“可也不能拿萱萱開刀啊。”
“在他們眼里,這可能根本不算‘開刀’。就像從一棵大樹上,掰個(gè)樹枝下來生火取暖,他們覺得樹那么大,少個(gè)樹枝沒什么。他們沒想過,那個(gè)樹枝,對(duì)樹來說,也是會(huì)疼的。”
他的比喻讓我心里一沉。是啊,在他們眼里,萱萱的人生才剛開始,有無限的可能,而我弟的人生已經(jīng)岌岌可危。用一點(diǎn)“可能性”,換一點(diǎn)“確定性”,在他們看來,是一筆劃算的買賣。
為了打破僵局,也為了證明不改名字我們也能幫忙,我開始瘋狂地幫我弟林浩留意工作機(jī)會(huì)。我動(dòng)用了自己工作以來積攢的所有人脈,請(qǐng)老同學(xué)、老同事吃飯,陪著笑臉,說盡了好話。
終于,一個(gè)在國(guó)企做HR的大學(xué)同學(xué)給了我消息,說他們公司有個(gè)新媒體運(yùn)營(yíng)的崗位,雖然不是正式編,但待遇不錯(cuò),問林浩愿不愿意試試。
我大喜過望,立刻把這個(gè)消息告訴了我媽。我特意沒有打電話,而是編輯了一條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微信,詳細(xì)說明了公司的背景、崗位職責(zé)和薪資待遇,末了還附上了那個(gè)同學(xué)的聯(lián)系方式。我想用這種方式告訴她,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很多種,不一定非要走那條最荒誕的路。
發(fā)完信息,我開始教她怎么用手機(jī)上的招聘軟件,把那個(gè)崗位收藏起來,方便她發(fā)給我弟看。
“媽,你看,點(diǎn)這里,這個(gè)五角星,點(diǎn)一下就收藏了。以后你在這里,‘我的收藏’里面,就能找到。”我耐心地在視頻通話里一步步演示。
她戴著老花鏡,瞇著眼睛湊近屏幕,顯得有些笨拙。“哦……哦……是這里嗎?”
“對(duì),就是那里。”
她操作成功后,卻沒有我預(yù)想中的高興,反而沉默了片刻,突然問我:“薈薈,這個(gè)軟件……能收到錢嗎?”
我一愣:“收錢?什么錢?”
“就是……別人要是給我轉(zhuǎn)一大筆錢,比如十幾萬,這里能收到嗎?”她問得小心翼翼。
我的心瞬間涼了半截。我費(fèi)盡心力找來的工作機(jī)會(huì),她關(guān)心的卻不是這個(gè),而是她那個(gè)虛無縹縹的“轉(zhuǎn)運(yùn)”夢(mèng)。她還在想著,只要萱萱改了名字,就會(huì)有一大筆錢從天而降,砸到她的賬戶上。
我無力地靠在椅子上,連話都不想說了。
“媽,那是個(gè)招聘軟件,不是支付軟件。”我疲憊地說,“工作的事,您讓我弟自己跟同學(xué)聯(lián)系吧。我很忙,先掛了。”
沒等她回話,我直接掐斷了視頻。
胸口那股無名火越燒越旺。我抓起車鑰匙就沖了出去。周誠(chéng)在后面喊我,我也沒有理會(huì)。
我把車開到一條無人的江邊公路上,停下來,然后狠狠一拳砸在方向盤上。
“憑什么!憑什么!”
眼淚不受控制地涌出來。我委屈,我憤怒,我更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。我以為我可以用實(shí)際行動(dòng)證明他們的錯(cuò)誤,結(jié)果卻發(fā)現(xiàn),我根本叫不醒一個(gè)裝睡的人。他們不是不明白道理,他們只是不愿意相信除了“借運(yùn)”之外,還需要付出其他的努力。
家不是講理的地方,但它應(yīng)該是可以呼吸的地方。而現(xiàn)在,我的原生家庭,已經(jīng)讓我無法呼吸。
不知過了多久,車窗被敲響了。我回頭一看,是周誠(chéng)。他不知什么時(shí)候跟了過來,手里還拿著一件我的外套。
我搖下車窗,他沒有說話,只是把外套披在我身上,然后坐進(jìn)了副駕駛。
狹小的車內(nèi)空間里,只有我壓抑的抽泣聲。
“想哭就哭出來吧。”他輕聲說。
我再也忍不住,趴在方向盤上嚎啕大哭。這些天所有的委屈、憤怒、失望,都隨著眼淚傾瀉而出。
周誠(chéng)沒有勸我,只是靜靜地陪著,偶爾用手拍拍我的背。
等我哭夠了,情緒慢慢平復(fù)下來,他才開口:“我剛給你弟打了個(gè)電話。”
我抬起紅腫的眼睛看著他。
“我問他,他一個(gè)三十歲的男人,躲在父母身后,讓父母為了他的前途,去逼自己的姐姐,犧牲自己外甥女的名字,他晚上睡得著覺嗎?”
我心里一驚:“他怎么說?”
“他沒說話。我就告訴他,工作的事,小薈已經(jīng)盡力了,路鋪到他腳下了,走不走是他自己的事。但如果他還由著爸媽這么鬧下去,那這個(gè)弟弟,我們也不認(rèn)了。周梓萱是我們家的底線,誰也別想碰。”
周誠(chéng)的語氣很平靜,但每個(gè)字都帶著不容置疑的力量。
我看著他,眼淚又一次模糊了視線。這一次,卻是溫暖的。
就在這時(shí),我的手機(jī)響了。是林浩打來的。我猶豫了一下,按了免提。
電話那頭,是我弟帶著哭腔的聲音:“姐,對(duì)不起。是我沒用,是我混蛋……你別生爸媽的氣了,我去跟他們說,名字不改了,什么都不改了……”
掛掉電話,我趴在周誠(chéng)的肩膀上,泣不成聲。
我以為,這件事,終于可以畫上句號(hào)了。
第三章
我終究是太天真了。
林浩的“幡然醒悟”并沒有持續(xù)多久。我不知道我媽又對(duì)他說了什么,或者承諾了什么,總之,僅僅過了一周,家里的氣氛就故態(tài)復(fù)萌,甚至變本加厲。
那天我?guī)е孑嫒ド显缃陶n,下課的時(shí)候,在機(jī)構(gòu)門口碰到了我媽。她像是等了很久,一看到我們出來,立刻迎了上來。
她沒有看我,徑直走到萱萱面前,蹲下身,從口袋里掏出一塊巧克力,笑得一臉慈愛:“麗麗,來,外婆給你買的好吃的。”
“麗麗”兩個(gè)字,像兩根鋼針,狠狠扎進(jìn)我的耳朵。
萱萱愣住了,她仰頭看著我,小臉上寫滿了困惑:“媽媽,外婆叫我什么?”
我心里的火“噌”地一下就冒了起來。我一把將萱萱拉到我身后,冷冷地看著我媽:“媽,她叫周梓萱。”
我媽臉上的笑容僵住了。她站起身,把巧克力塞回口袋,看著我,眼神里沒有了之前的懇求,只剩下一種近乎偏執(zhí)的固執(zhí)。
“早晚都得改,我先叫習(xí)慣了不行嗎?”
“不行!”我?guī)缀跏呛鸪鰜淼摹?/p>
周圍的家長(zhǎng)和孩子紛紛向我們投來異樣的目光。我感到一陣難堪,拉著萱萱的手轉(zhuǎn)身就走。
“林薈!”我媽在身后喊道,“你別不識(shí)好歹!我這都是為了誰?要不是為了你弟,為了這個(gè)家,我用得著低聲下氣地求你嗎?你以為我想這樣嗎?你弟昨天又被領(lǐng)導(dǎo)罵了,他說那個(gè)項(xiàng)目做不下來,可能要被辭退!你說我能不急嗎?”
我停下腳步,沒有回頭。
“那是他的事。他三十歲了,不是三歲。他該為自己的人生負(fù)責(zé)了。”
“他怎么負(fù)責(zé)?他拿什么負(fù)責(zé)?沒錢沒房沒背景,他拿頭去負(fù)責(zé)嗎?”我媽的聲音越來越激動(dòng),甚至帶上了一絲方言的腔調(diào),“我們不就指望你們拉他一把嗎?你倒好,翅膀硬了,連親媽親弟都不認(rèn)了!”
我深吸一口氣,拉著萱萱快步離開,把她的哭喊和咒罵遠(yuǎn)遠(yuǎn)地甩在身后。
回到家,我把萱萱安頓好,整個(gè)人都像被抽空了力氣。周誠(chéng)回來時(shí),看到的就是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沙發(fā)上的樣子。
他什么也沒問,只是走過來,從背后抱住我。
“又去找你了?”
我點(diǎn)點(diǎn)頭,把臉埋在他寬厚的肩膀里。
“別怕,有我呢。”他說。
那天晚上,我們爆發(fā)了結(jié)婚以來最激烈的一次爭(zhēng)吵。
起因是我說:“要不,我們還是給他們點(diǎn)錢吧。二十萬,夠我弟首付了。給了錢,他們是不是就不會(huì)再糾結(jié)名字的事了?”
這是我的妥協(xié),也是我的懦弱。我太想結(jié)束這場(chǎng)無休止的拉鋸戰(zhàn)了,我想用錢,買一個(gè)清靜。
周誠(chéng)的臉?biāo)查g就冷了下去。“林薈,你還沒明白嗎?這不是錢的事!”
“那是什么事?”我激動(dòng)地站起來,“不就是嫌我弟沒錢買房嗎?我們給他錢不就行了!”
“不行!”他斬釘截鐵地說,“今天你因?yàn)楦拿氖峦讌f(xié)給了二十萬,明天他們就能因?yàn)槟愕軗Q工作再要三十萬!他們的欲望是個(gè)無底洞,你拿什么填?拿我們的生活,拿萱萱的未來去填嗎?”
“那怎么辦?就這么僵著嗎?周誠(chéng),你知不知道我快被逼瘋了!”我失控地喊道。
“瘋?我才要瘋!”他也提高了音量,“你是我老婆,萱萱是我女兒!我憑什么要讓我的老婆孩子受這種委屈?就因?yàn)槟隳莻€(gè)不爭(zhēng)氣的弟弟,和你那對(duì)拎不清的父母?”
“他們是我爸媽!”我吼了回去。
“他們是你爸媽,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嗎?就可以打著為你好的旗號(hào),理直氣壯地傷害你,傷害我們的女兒?jiǎn)幔俊?/p>
爭(zhēng)吵在狹小的客廳里回蕩,每一個(gè)字都像一把刀子,割得我體無完膚。
“你根本不理解我!”
“是你從沒想過讓我理解!你總是一個(gè)人扛,一個(gè)人妥協(xié)!林薈,你什么時(shí)候才能為你自己,為我們這個(gè)小家,硬氣一次?”
我們倆都?xì)饧t了眼,互相瞪著對(duì)方,胸口劇烈地起伏。
最后,我啞著嗓子說:“我累了,我不想吵了。”
說完,我轉(zhuǎn)身走進(jìn)了臥室,反鎖了房門。
沉默,是成年人最響亮的哭聲。
我沒有開燈,就那么靠在門后,緩緩地滑坐到地上。黑暗中,我聽見客廳里傳來周誠(chéng)煩躁的踱步聲,然后是打火機(jī)“咔噠”一聲,他很少抽煙。
我們進(jìn)入了冷戰(zhàn)。
我們睡在同一張床上,卻隔著一個(gè)太平洋的距離。他晚上回來,會(huì)把晚飯熱好放在桌上,然后自己回書房。我半夜渴醒,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床頭柜上永遠(yuǎn)放著一杯溫度剛好的水。他早上出門前,會(huì)把萱萱的早餐準(zhǔn)備好,放在保溫盒里。
這些無聲的關(guān)懷,像一根根細(xì)密的針,扎得我心里又疼又軟。
我開始失眠,整夜整夜地睡不著。一天凌晨,我悄悄起床,想去客廳喝水,卻發(fā)現(xiàn)書房的門縫里還透著光。
我鬼使神差地走了過去,門沒有關(guān)嚴(yán),留著一道縫。我看到周誠(chéng)坐在電腦前,屏幕上是一個(gè)購(gòu)房網(wǎng)站。他在看一個(gè)離我們家不遠(yuǎn),但學(xué)區(qū)和環(huán)境都差了很多的老破小。
總價(jià),一百二十萬。首付,三十六萬。
我的心,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,疼得無法呼吸。
我突然明白,他不是不理解我的為難,他不是不愿意幫忙。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,守護(hù)著我們這個(gè)家的底線和尊嚴(yán)。他查的那個(gè)房子,價(jià)格和地段,分明是為我弟準(zhǔn)備的。他嘴上說著不妥協(xié),卻在背后,默默地為我的懦弱和為難,尋找著一個(gè)最不傷害我們小家的解決方案。
我捂住嘴,不讓自己哭出聲,悄悄退回了臥室。
躺在床上,我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,直到天光大亮。
我做了一個(gè)決定。
第二天一早,我對(duì)我媽說,我同意了。
我同意帶萱萱去派出所,把“周梓萱”改成“周麗”。
第四章
當(dāng)我把這個(gè)決定告訴周誠(chéng)時(shí),他臉上的表情,我一輩子都忘不了。
那是一種混雜著震驚、失望、憤怒和徹骨寒心的復(fù)雜神情。他死死地盯著我,看了足足有半分鐘,然后,他笑了。那笑聲很輕,卻像玻璃碎裂的聲音,刺得我耳膜生疼。
“林薈,你真是……好樣的。”他一字一頓地說完,轉(zhuǎn)身就走,摔門的聲音震得整棟樓都仿佛晃了一下。
我知道,我傷透了他的心。
我何嘗不知道這是飲鴆止渴?我何嘗不知道這是對(duì)我女兒最殘忍的剝奪?可我被逼到了懸崖邊上。一邊是丈夫的失望,一邊是父母以死相逼的決絕。我媽甚至在我面前吞了一把降壓藥,幸虧發(fā)現(xiàn)及時(shí)送去洗胃,才沒出大事。
我爸指著我的鼻子罵:“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們才甘心?你弟的前途,你媽的命,都比不上一個(gè)破名字重要嗎?”
我的精神防線,在那一刻,徹底崩潰了。
我像一個(gè)提線木偶,被我媽拉著,機(jī)械地準(zhǔn)備著改名需要的各種材料。戶口本、出生證明、父母雙方的身份證……
我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抽屜,都沒有找到我們的戶口本。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一個(gè)可怕的念頭冒了出來。
我沖進(jìn)書房,周誠(chéng)出差了,要一周才回來。我把他平時(shí)放重要文件的那個(gè)抽屜拉開,里面是空的。
戶口本不見了。
我瘋了一樣地給周誠(chéng)打電話,電話接通了,他的聲音冷得像冰。
“戶口本呢?”我急切地問。
“我拿了。”
“你拿了?周誠(chéng),你把它放哪兒了?你快給我!”
電話那頭是一陣長(zhǎng)久的沉默,久到我以為他已經(jīng)掛了。然后,我聽見他疲憊至極的聲音:“林薈,你非要這樣嗎?非要把我們這個(gè)家,拆了才甘心嗎?”
“我不想!可是我能怎么辦?我媽她……”
“她用死逼你,你就要用我們女兒的一輩子去換嗎?”他打斷我,聲音陡然嚴(yán)厲起來,“我告訴你,戶口本我?guī)ё吡恕V灰也煌猓@個(gè)名字,誰也改不了!你要是敢偽造文件,我們就法庭上見!”
“離婚”兩個(gè)字,他雖然沒說出口,但我聽懂了。
我握著電話,癱坐在地上,嚎啕大哭。
就在我絕望之際,萱萱房間的門開了。她揉著惺忪的睡眼走出來,懷里抱著她最喜歡的小熊玩偶。
“媽媽,你怎么了?你別哭。”她走到我身邊,用她小小的手,笨拙地擦著我臉上的淚。
我一把將她摟進(jìn)懷里,哭得更兇了。
萱萱被我嚇到了,也跟著哭了起來。她一邊哭一邊說:“媽媽,是不是因?yàn)槲也还裕渴遣皇且驗(yàn)椤驗(yàn)橥馄沤形摇慃悺也桓吲d,所以你才哭的?”
她仰起掛著淚珠的小臉,用一種近乎討好的語氣,小心翼翼地說:“媽媽,你別哭了……如果……如果叫‘麗oli’你能不哭,那……那我就叫周麗好了。我不喜歡周梓萱了,我喜歡周麗……”
轟!
我感覺我的腦袋像是被炸開了一樣。
我的女兒,我五歲的女兒,她在用她全部的愛,來安慰我,來遷就我。她以為是我不喜歡她的名字,她以為是她惹我生氣了。為了讓我開心,她愿意放棄那個(gè)她曾經(jīng)一筆一劃、驕傲地寫在紙上的名字。
我到底在做什么?
我為了平息父母的焦慮,為了所謂的家庭和睦,竟然把我的女兒逼到了這個(gè)地步!我讓她以為,她的存在,她的名字,是錯(cuò)誤的,是需要被修正的。
人最怕的,就是用‘為你好’的名義,親手折斷你的翅膀。
而我,差一點(diǎn)就成了那個(gè)親手折斷我女兒翅膀的劊子手。
我用力地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,仿佛要把肺里所有的懦弱和猶豫都吐出去。我擦干眼淚,捧著萱萱的小臉,無比鄭重地對(duì)她說:“不,寶貝。你聽媽媽說。你叫周梓萱,永遠(yuǎn)都叫周梓萱。這是爸爸媽媽送給你最好的禮物,誰也搶不走。媽媽剛才哭,不是因?yàn)槟悖且驗(yàn)閶寢屪约鹤鲥e(cuò)了事。對(duì)不起,是媽媽不好。”
萱萱似懂非懂地點(diǎn)點(diǎn)頭,用小手拍拍我的臉:“媽媽不哭,萱萱愛媽媽。”
我抱著她,心里那塊懸了很久的巨石,終于落了地。
我做出了選擇。
我給周誠(chéng)發(fā)了條信息:【對(duì)不起。等我處理好。】
然后,我撥通了我媽的電話。
“媽,我在小區(qū)的咖啡館等你,有些事,我們必須當(dāng)面說清楚。”
第五章
咖啡館里,冷氣開得很足。
我媽坐在我對(duì)面,神情倨傲,像一個(gè)得勝的將軍。她大概以為,我是來跟她商量去派出所的具體時(shí)間的。
我把一杯檸檬水推到她面前,開門見山:“媽,萱萱的名字,不改了。”
她臉上的笑容瞬間凝固,取而代之的是不敢置信的憤怒。“你說什么?林薈,你耍我玩呢?”
“我沒有耍你。”我的聲音很平靜,平靜得連我自己都感到意外,“就在剛才,萱萱跟我說,如果我喜歡,她可以叫周麗。她以為,是我不喜歡她的名字。”
我看著我媽的眼睛,一字一頓地說:“媽,她才五歲。我們大人之間的博弈和貪婪,憑什么要讓她來承擔(dān)后果?憑什么要讓她用否定自己的方式,來換取我們的安寧?”
我媽的嘴唇哆嗦著,說不出話來。
“為了給弟弟‘借運(yùn)’,你們就要奪走她與生俱來的東西。你們有沒有想過,這對(duì)她有多不公平?運(yùn)勢(shì)這種東西,虛無縹緲,可是一個(gè)人的名字,會(huì)跟隨她一輩子!當(dāng)她長(zhǎng)大后,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被家人為了一個(gè)荒唐的理由犧牲掉的,她會(huì)怎么想?她會(huì)怎么看待我們這些所謂的親人?”
“我……”
“你們總說,是為了阿浩好,為了這個(gè)家好。可你們所謂的‘好’,是建立在另一個(gè)家庭成員的犧牲之上的。這不是愛,這是綁架,是掠奪!”
我的聲音不大,但每個(gè)字都像一顆釘子,釘進(jìn)我們之間那張薄薄的桌面。
“林薈!你這是在教訓(xùn)我嗎?”我媽終于反應(yīng)過來,猛地一拍桌子,咖啡濺了出來,“我是你媽!我吃的鹽比你吃的米都多!我做什么不是為了你們好?你弟要是過得不好,我們老兩口將來怎么辦?我們死了都閉不上眼!”
她的口頭禪又來了,“都是為你好”。以前,這句話是溫暖的港灣;后來,是沉重的枷鎖;而現(xiàn)在,我只覺得無比諷刺。
“那不是我該考慮的問題。”我冷冷地說,“阿浩已經(jīng)三十歲了,他的人生,應(yīng)該由他自己負(fù)責(zé)。你們可以愛他,可以幫他,但不可以犧牲我的女兒去填他的窟窿。”
“你……你這個(gè)不孝女!”我媽氣得渾身發(fā)抖,指著我的鼻子,“我算是看透了,你就是個(gè)白眼狼!為了你那個(gè)小家,連自己的親媽親弟都不要了!”
“對(duì)。”我點(diǎn)點(diǎn)頭,迎著她震驚的目光,“如果非要我在我的小家和你們的貪心中選一個(gè),我選我的家。如果非要我在我女兒的幸福和弟弟的前途中選一個(gè),我選我的女兒。如果守護(hù)他們,意味著要成為你們眼中的‘不孝女’和‘白眼狼’,那我認(rèn)了。”
拔掉一顆爛牙會(huì)疼,但不拔,爛掉的是整個(gè)口腔。
我的原生家庭,就是那顆爛牙。而我,今天必須親手把它拔掉。
我媽被我這番話徹底鎮(zhèn)住了。她大概從沒想過,那個(gè)一向溫順、聽話的女兒,會(huì)說出如此決絕的話。她張著嘴,想罵什么,卻一個(gè)字也吐不出來。
我從包里拿出一張銀行卡,推到她面前。
“這里面有五萬塊錢。是我和周誠(chéng)的一點(diǎn)心意,不是給阿浩買房的,是給你們二老養(yǎng)老的。密碼是你的生日。”
“我們不需要你的臭錢!”她像被燙到一樣,把卡甩了回來。
我沒有去撿。“錢我放在這里。從今天起,我會(huì)每個(gè)月給你們打三千塊錢作為贍養(yǎng)費(fèi)。這是我作為女兒的義務(wù)。其他的,我無能為力。”
我站起身,居高臨下地看著她:“媽,別再試圖向孩子‘借運(yùn)’了。你每借一次,孩子的人生就會(huì)被剝掉一層皮,越來越差。萱萱的運(yùn),是她自己的,誰也借不走。阿浩的運(yùn),也在他自己手里,不在他外甥女的名字里。”
說完,我沒再看她一眼,轉(zhuǎn)身走出了咖啡館。
推開門,外面陽光燦爛,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,空氣里沒有了那股熟悉的、令人窒息的味道。
我自由了。
第六章
我以為,我的決絕會(huì)換來一場(chǎng)曠日持久的家庭戰(zhàn)爭(zhēng),甚至是我父母徹底的斷絕關(guān)系。
但出乎我意料的是,一切都平靜得可怕。
我媽沒有再給我打電話,也沒有再出現(xiàn)在我家門口或者萱萱的早教班。我按月打過去的贍養(yǎng)費(fèi),她沒有退回。那張五萬塊的卡,后來我查了流水,也被取空了。
就好像,我們之間達(dá)成了一種詭異的默契。他們接受了我的錢,也默認(rèn)了我的“不孝”。我們成了一對(duì)靠金錢維系著最基本血緣關(guān)系的母女。
只有電視機(jī)的音量,泄露了某些真相。
有一次我因?yàn)橐鸵环菸募樎坊亓颂四锛摇i_門的是我爸,他看到我,愣了一下,然后默默地讓開了身子。
客廳里,電視機(jī)開著,音量調(diào)到了45。
那是一個(gè)震耳欲聾的數(shù)字。我媽坐在沙發(fā)上,眼神空洞地盯著屏幕,屏幕上花花綠綠的綜藝節(jié)目,顯然沒能進(jìn)入她的眼睛。她瘦了很多,兩頰深陷,頭發(fā)也白了大半。
看到我,她只是抬了抬眼皮,沒說話。
我把文件放在玄關(guān)的柜子上,輕聲說:“我來拿個(gè)東西,馬上就走。”
沒有人回應(yīng)我。
我走進(jìn)我以前的房間,找到了那份文件。出來的時(shí)候,我爸叫住了我。
他遞給我一個(gè)信封,很厚。
“這是那五萬塊。”他聲音沙啞,“我們還沒到要靠賣外孫女名字過活的地步。”
我沒接。
“拿著吧。”他把信封塞進(jìn)我手里,“你媽……病了。醫(yī)生說是抑郁癥。她現(xiàn)在誰的話都聽不進(jìn)去,整天就是發(fā)呆,或者看電視,把聲音開到最大。”
我的心,像被針扎了一下。
“她總說,家里太靜了,靜得瘆人。她想聽點(diǎn)響動(dòng)。”我爸別過臉去,我看到他渾濁的眼睛里,閃著一絲水光,“你弟……林浩,他上個(gè)月辭職了。你同學(xué)介紹的那個(gè)工作,他干了不到倆月,嫌累,不干了。現(xiàn)在天天在家打游戲。”
我握著那個(gè)信封,只覺得無比沉重。
“那先生說的話,好像都應(yīng)驗(yàn)了。”我爸喃喃自語,“家里破財(cái),你弟倒霉……是不是……是不是我們當(dāng)初真的做錯(cuò)了?”
我看著他蒼老的面容,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我沒有拿那筆錢,我把它重新放在了柜子上。“爸,帶我媽好好看病。錢不夠,隨時(shí)跟我說。”
走出那個(gè)家,我的腳步無比沉重。我贏了嗎?我好像贏了,我守護(hù)了我的女兒,守護(hù)了我的小家。可看著父母的蒼老和弟弟的墮落,我心里沒有一絲勝利的喜悅,只有一片化不開的悲涼。
周誠(chéng)出差回來了。
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。他抱著我,很久都沒有說話。
那天晚上,我們躺在床上,第一次心平氣和地談起這件事。
“周誠(chéng),我是不是很自私?”我問。
“不。”他握住我的手,很用力,“你只是做了一個(gè)母親該做的事。保護(hù)自己的孩子,是本能,不是自私。”
“可我媽病了,我弟也……我總覺得,如果我當(dāng)初……”
“沒有如果。”他打斷我,“林薈,你聽著。就算你妥協(xié)了,改了名字,給了錢,你覺得一切就會(huì)好起來嗎?不會(huì)的。一個(gè)好吃懶做、指望天上掉餡餅的弟弟,一個(gè)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虛無縹緲的‘運(yùn)勢(shì)’上的家庭,就像一個(gè)沼澤,你陷進(jìn)去,只會(huì)被拖得越來越深,直到你和萱萱都被吞噬。”
他頓了頓,聲音變得很柔:“你做的,是止損。是把你和萱萱,從那個(gè)沼澤里,拔了出來。”
【第三人稱視角】
深夜,林浩的房間里只有鍵盤和鼠標(biāo)的敲擊聲。屏幕上,游戲人物正在進(jìn)行一場(chǎng)激烈的廝殺。
他媽推門進(jìn)來,端著一碗熱氣騰騰的面。
“阿浩,吃點(diǎn)東西吧,你一天沒吃飯了。”
林浩頭也不回,不耐煩地“嗯”了一聲。
他媽把面放在桌上,看著他沉迷游戲的樣子,欲言又止。過了一會(huì)兒,她才小聲說:“你姐今天回來了。”
林浩的動(dòng)作頓了一下。
“她……她給你爸媽錢了。讓你媽去看病。”
“哦。”林浩的反應(yīng)很平淡,仿佛在聽一件與自己無關(guān)的事。
“阿浩,你……就沒什么想法?”
“什么想法?讓我去謝謝她?還是讓我去給她下跪道歉?”林浩冷笑一聲,“她現(xiàn)在是人生贏家,老公能干,女兒可愛,我們算什么?不過是她成功路上的絆腳石,是她需要擺脫的累贅。”
“別這么說你姐……”
“我說的有錯(cuò)嗎?”林浩猛地轉(zhuǎn)過椅子,眼睛里布滿血絲,“當(dāng)初是誰跟我說,只要改了名字,一切都會(huì)好起來?現(xiàn)在呢?名字沒改成,我工作丟了,媽你病了,家里雞飛狗跳!這就是你說的‘好起來’?”
他媽被他吼得一個(gè)哆嗦,眼淚掉了下來。
林浩看著她,心里的煩躁和怨恨像野草一樣瘋長(zhǎng)。他抓起桌上的那碗面,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“我不要你們的‘為我好’!我變成今天這樣,都是被你們害的!”
瓷碗碎裂的聲音,在寂靜的夜里,格外刺耳。
【第一人稱視角】
我和周誠(chéng)的關(guān)系,在經(jīng)歷了這場(chǎng)風(fēng)暴后,反而變得更加緊密。我們都明白了,這個(gè)小小的三口之家,才是我們最需要守護(hù)的陣地。
為了讓萱萱徹底擺脫這件事的影響,我們帶她去了一趟海邊。
在黃昏的沙灘上,我和周誠(chéng)牽著萱萱的手,一起看日落。
萱萱突然問:“爸爸媽媽,我的名字,是不是很好聽?”
周誠(chéng)蹲下來,把她抱進(jìn)懷里,認(rèn)真地對(duì)她說:“對(duì)。周梓萱,是這個(gè)世界上最好聽的名字。‘梓’,是百木之王,代表堅(jiān)強(qiáng)和挺拔。‘萱’,是忘憂草,代表快樂和無憂。爸爸媽媽希望你,能像大樹一樣堅(jiān)強(qiáng),永遠(yuǎn)快樂無憂。”
萱萱似懂非懂地點(diǎn)點(diǎn)頭,開心地笑了。
我看著他們父女倆,眼眶濕潤(rùn)了。
夕陽的余暉灑在海面上,金光粼粼。我知道,有些傷痕,可能永遠(yuǎn)無法完全愈合。但生活,終究要向前看。
第七章
日子像流沙,不經(jīng)意間,又過去了一年。
這一年里,我和娘家的關(guān)系,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。我依舊按月打錢,逢年過節(jié)會(huì)送些東西過去,但人很少回去。偶爾通個(gè)電話,也只是三言兩語的問候,我媽接電話的時(shí)候少,多半是我爸。
他說,我媽的抑郁癥時(shí)好時(shí)壞,藥一直吃著。林浩依舊待在家里,靠我們給的和我爸媽的退休金過活,偶爾在網(wǎng)上做點(diǎn)代練賺些零花錢,徹底成了一個(gè)“蹲族”。
那個(gè)家,仿佛成了一個(gè)巨大的黑洞,慢慢吞噬著所有人的生命力。
萱萱上幼兒園了。她活潑開朗,是老師最喜歡的小朋友之一。她很喜歡自己的名字,每次在作業(yè)本上寫下“周梓萱”三個(gè)字,都一筆一劃,格外認(rèn)真。那件事留下的陰影,似乎已經(jīng)在她小小的世界里,徹底消散了。
只有我知道,那道疤痕,刻在了我的心里。
我時(shí)常會(huì)做夢(mèng),夢(mèng)見五歲的萱萱,用討好的語氣對(duì)我說:“媽媽,我叫周麗好了。”每一次,我都會(huì)從夢(mèng)中驚醒,一身冷汗。
周誠(chéng)說,這是我的心結(jié)。
或許吧。
初夏的一個(gè)清晨,我正在陽臺(tái)上給花澆水。陽光很好,微風(fēng)不燥。周誠(chéng)在廚房做早餐,平底鍋上煎蛋的“滋滋”聲,和萱萱在客廳里看動(dòng)畫片的笑聲,交織成一首最動(dòng)聽的晨曲。
手機(jī)響了,是我爸打來的。
他的聲音聽起來異常疲憊和蒼老。
“薈薈,你……有空嗎?你媽她……她想見見萱萱。”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這是兩年來,他們第一次主動(dòng)提出要見萱萱。
“她怎么了?”
“沒什么……就是念叨。她說,好久沒見外孫女了。”
我沉默了。理智告訴我,應(yīng)該拒絕。我好不容易才把萱萱從那個(gè)旋渦里拉出來,我不想她再受到任何影響。
可電話那頭,我爸的呼吸聲,沉重得像一臺(tái)破舊的風(fēng)箱。我仿佛能看到他佝僂著背,滿臉愁容的樣子。
掛掉電話,我走進(jìn)廚房。
周誠(chéng)正在把煎好的雞蛋盛到盤子里。他看到我的臉色,問:“怎么了?”
“我爸打來的,說我媽想見萱萱。”
周誠(chéng)的動(dòng)作停住了。他沒有立刻表態(tài),只是看著我。
“你怎么想?”他問。
我搖搖頭:“我不知道。我怕……”
“怕她又提改名的事?”
“不,她應(yīng)該不會(huì)了。我怕……我怕萱萱看到他們現(xiàn)在的樣子,會(huì)害怕。也怕他們看到萱萱,又會(huì)想起那些不好的事。”
周誠(chéng)擦了擦手,走到我面前,輕輕擁抱了我一下。
“去吧。”他說,“帶著萱萱去。不是為了他們,是為了你自己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你這個(gè)心結(jié),總要解開的。”他看著我的眼睛,目光溫和而堅(jiān)定,“血緣是斷不了的。你可以選擇不原諒,但你需要去面對(duì)。面對(duì)了,才能真正放下。”
他繼續(xù)說:“而且,也該讓萱萱知道,這個(gè)世界不全是陽光和早餐。有些親人,會(huì)犯錯(cuò),會(huì)生病,會(huì)變得不可理喻。但這不代表,我們就要否定那份曾經(jīng)存在過的愛。讓她去看看,讓她自己去感受。相信我們的女兒,她比你想象的要堅(jiān)強(qiáng)。”
我看著周誠(chéng),心里那塊一直懸著的石頭,好像突然有了支撐。
下午,我?guī)е孑嫒チ四锛摇?/p>
開門的一瞬間,我?guī)缀醪桓蚁嘈抛约旱难劬Α?/p>
家里很亂,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藥味和食物餿掉的混合氣味。我媽坐在沙發(fā)上,呆呆地看著電視。
電視機(jī)是關(guān)著的,黑色的屏幕上,映出她蒼老而憔悴的臉。
她瘦得脫了相,穿著一件不合身的舊衣服,頭發(fā)花白,眼神渾濁。那個(gè)曾經(jīng)精明、強(qiáng)勢(shì)、永遠(yuǎn)要把一切都掌控在手里的女人,消失了。眼前的,只是一個(gè)被生活徹底擊垮的老人。
看到我們,她沒有任何反應(yīng),依舊看著那個(gè)黑色的屏幕。
萱萱有些害怕,緊緊攥著我的手,躲在我身后。
我爸從房間里走出來,沖我苦笑了一下,然后蹲下身,對(duì)萱萱招招手:“萱萱,還記得外公嗎?”
萱萱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,小聲說:“外公好。”
我爸的眼圈一下子就紅了。
我拉著萱萱,走到沙發(fā)前。
“媽,我們來看你了。”
我媽的眼球動(dòng)了動(dòng),慢慢地,慢慢地轉(zhuǎn)向萱萱。她的目光在萱萱臉上停留了很久,渾濁的眼睛里,似乎有了一絲光亮。
她伸出干枯的手,顫顫巍巍地,想要去摸一摸萱萱的臉。
萱萱下意識(shí)地往后縮了一下。
我的心揪了起來。
然而,我媽的手,在半空中停住了。她看了看自己滿是褶皺和斑點(diǎn)的手,又看了看萱萱粉嫩光滑的小臉,然后,默默地把手收了回去。
她張了張嘴,喉嚨里發(fā)出“嗬嗬”的聲音,像是有什么東西堵住了。過了好半天,她才用一種近乎耳語的聲音,說出了兩個(gè)字。
“……萱萱。”
不是“麗麗”,是“萱萱”。
那一刻,我所有的怨恨、憤怒、委屈,都像被抽空了一樣。
我蹲下身,握住她冰冷的手:“媽,是我,林薈。我們來看你了。”
她沒有看我,眼睛還是一瞬不瞬地盯著萱萱,嘴里反復(fù)地、模糊不清地念著:“萱萱……我的……萱萱……”
眼淚,從她干涸的眼角,滾落下來。
我們沒有待太久。林浩始終沒有從他的房間里出來。
回家的路上,萱萱一直很沉默。
快到家時(shí),她突然問我:“媽媽,外婆是不是生病了?”
我點(diǎn)點(diǎn)頭:“是,外婆生了很重的病。”
“那……她會(huì)好起來嗎?”
“會(huì)的。”我說,“只要好好吃藥,好好休息,就會(huì)慢慢好起來的。”
萱萱“哦”了一聲,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。過了一會(huì)兒,她又小聲說:“媽媽,外婆剛才哭了。她看起來好可憐。”
我摸了摸她的頭,沒有說話。
回到家,夕陽正從窗戶照進(jìn)來,把客廳染成一片溫暖的橘色。周誠(chéng)已經(jīng)下班回來了,正在廚房里忙碌。
萱萱跑過去,抱住他的腿:“爸爸,我回來了!”
周誠(chéng)笑著把她抱起來,親了一口。
我站在玄關(guān),看著眼前這幅溫馨的畫面,心里五味雜陳。
我走到廚房門口,靠在門框上。周誠(chéng)正在切菜,刀刃和砧板碰撞,發(fā)出清脆而有節(jié)奏的聲響。
他感覺到了我的目光,回過頭來,沖我笑了笑。
我想對(duì)他說些什么。
或許是“謝謝你”,謝謝他一直以來的支持和理解。
或許是“對(duì)不起”,為我曾經(jīng)的懦弱和動(dòng)搖。
又或許,只是一句簡(jiǎn)單的,“我愛你”。
可我張了張嘴,最終什么也沒說出口。
我只是走過去,從背后輕輕地抱住了他。我把臉貼在他寬闊而溫暖的后背上,閉上眼睛,靜靜地聽著那熟悉而安心的切菜聲,聽著客廳里女兒銀鈴般的笑聲。
窗外,最后一抹晚霞,正溫柔地?fù)肀е@個(gè)城市。
我知道,生活還要繼續(xù)。有些結(jié),或許永遠(yuǎn)解不開,但我們,已經(jīng)學(xué)會(huì)了帶著它,繼續(xù)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