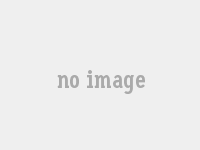去了趟新疆阿克蘇,真心建議:不要隨便去阿克蘇,除非你知道這些
去了趟新疆阿克蘇,真心建議:不要隨便去阿克蘇,除非你知道這些。
這些不是指最佳的旅游路線,也不是哪家烤肉最正宗,更不是關(guān)于冰糖心蘋果的甜度報(bào)告。
這些,是關(guān)于一個(gè)男人的沉默,一個(gè)女人的等待,和一個(gè)被風(fēng)沙掩埋了近五十年的秘密。
故事,要從我父親的葬禮后說(shuō)起。
父親走得很突然,心梗,在睡夢(mèng)中。沒有留下任何遺言,就像他沉默了一輩子那樣,把所有的話都帶走了。我們整理遺物時(shí),在書房最高一格,他那本翻爛了的《資治通鑒》里,找到了一把小小的,已經(jīng)泛出銅銹的鑰匙。
母親盯著那把鑰匙,眼神很復(fù)雜。她沒說(shuō)話,只是用指甲掐著自己的掌心,一個(gè)我從小看到大的習(xí)慣性動(dòng)作。我知道,她心里有事,但她不說(shuō),我也從不敢問。
這把鑰匙打開的,是床底下一個(gè)上了鎖的錫皮盒子。盒子打開的瞬間,一股樟腦和舊紙張混合的味道撲面而來(lái),像是某個(gè)塵封的時(shí)代被瞬間喚醒。
盒子里沒有存折,沒有房產(chǎn)證,只有一沓泛黃的信,幾枚毛主席像章,一本空白的日記本,以及……一張照片。
照片上,是年輕時(shí)的父親。他穿著那個(gè)年代的舊軍裝,笑得一臉燦爛,牙齒雪白。他身旁,站著一個(gè)梳著兩條長(zhǎng)辮子的維吾爾族姑娘,她的眼睛像阿克蘇的湖水,清澈見底。他們身后,是一大片金黃色的胡楊林。
那不是我母親。
我下意識(shí)地去看母親的臉。她的表情很平靜,平靜得像結(jié)了冰的湖面。她拿起那張照片,指尖輕輕撫過父親年輕的臉龐,然后,一句話沒說(shuō),轉(zhuǎn)身進(jìn)了廚房。很快,里面?zhèn)鱽?lái)嘩嘩的水流聲,她好像在洗什么東西,洗了很久很久。
我拿起那本空白的日記本,翻到最后一頁(yè),才發(fā)現(xiàn)父親用鋼筆寫下的一行字,字跡潦草,仿佛用盡了全身的力氣:
“阿克蘇,一生的約定,成了一生的虧欠。”
那一刻,我心里某個(gè)堅(jiān)固的東西,碎了。我一直以為,我的父親,李建國(guó),是一個(gè)再普通不過的男人。他是工程師,嚴(yán)謹(jǐn),刻板,沉默寡言。他愛我,也愛母親,但他的愛像一杯溫吞的白開水,從不沸騰。我以為這就是他的全部。
原來(lái)不是。
【情感地雷一:母親異常的平靜】
【情感地雷二:那張不屬于母親的照片】
【情感地雷三:日記本里那句沒頭沒尾的遺言】
我把照片和日記本收了起來(lái),沒讓丈夫陳陽(yáng)看見。那天晚上,我失眠了。我看著身邊熟睡的丈夫,突然覺得無(wú)比陌生。我們結(jié)婚十年,他了解我的一切嗎?就像我,自以為很了解我的父親。
第二天,我跟公司請(qǐng)了年假,訂了兩張去阿克蘇的機(jī)票。
陳陽(yáng)問我:“怎么突然想去新疆?那邊現(xiàn)在很冷。”
我把照片和日記本拿給他看,說(shuō):“我想去看看,我爸這輩子,到底虧欠了什么。”
出發(fā)前,我跟母親攤牌。她正在陽(yáng)臺(tái)擦拭那盆她養(yǎng)了二十年的君子蘭,葉片被她擦得油光發(fā)亮。
“媽,我要和陳陽(yáng)去一趟阿克蘇。”
她擦拭的動(dòng)作停頓了一下,只有一下,然后繼續(xù),頭也沒回。
“去吧,外面冷,多穿點(diǎn)。”
“媽,”我忍不住提高了聲音,“你沒什么想問的嗎?”
她終于轉(zhuǎn)過身,看著我,眼神里有一種我看不懂的疲憊。“小冉,人這一輩子,不知道一些事,會(huì)活得輕松點(diǎn)。你爸……他是個(gè)好人。”
她說(shuō)完,又轉(zhuǎn)過身去,繼續(xù)擦那片葉子,一遍又一遍,仿佛要把它擦穿。
我知道,我必須去。不僅是為了父親,也是為了我自己。我想知道,在那片遙遠(yuǎn)的土地上,究竟藏著一個(gè)怎樣的故事,能讓一個(gè)男人至死不忘,能讓一個(gè)女人守口如瓶。
阿克蘇的機(jī)場(chǎng)很小,風(fēng)很大。走出航站樓的瞬間,一股干冷凌厲的風(fēng)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。天空是那種不含一絲雜質(zhì)的藍(lán),遼闊,高遠(yuǎn),讓人心生敬畏,也倍感孤獨(dú)。
這就是父親年輕時(shí)待過的地方。
我們手里唯一的線索,就是那張照片,和一個(gè)可能的名字。我猜,那個(gè)姑娘叫阿依古麗,或者古麗娜扎,所有我想象中美好的維吾爾族名字。照片背后,用鉛筆寫著一個(gè)地址:紅旗公社三大隊(duì)。
可如今的阿克蘇,哪里還有什么紅旗公社。
我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,陳陽(yáng)負(fù)責(zé)上網(wǎng)查資料,我負(fù)責(zé)對(duì)著那張照片發(fā)呆。照片上的父親,那么年輕,那么鮮活,他的笑容里有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光。那是在我的記憶里,他臉上從未出現(xiàn)過的神采。
接下來(lái)的兩天,我們像無(wú)頭蒼蠅一樣在阿克蘇市區(qū)亂轉(zhuǎn)。我們?nèi)チ瞬┪镳^,去了地方志辦公室,試圖找到關(guān)于“紅旗公社”的線索。工作人員很熱情,但年代久遠(yuǎn),資料缺失,他們能提供的幫助有限。
“五六十年代來(lái)我們這兒的支邊青年太多了,上海來(lái)的,北京來(lái)的,一撥一撥的。后來(lái)大多都回去了。”一位頭發(fā)花白的老研究員告訴我們。
我拿出那張翻拍在手機(jī)里的照片給他看。他戴上老花鏡,湊得很近,看了半天,搖了搖頭。“丫頭啊,這胡楊林,我們阿克蘇到處都是。這姑娘……也沒什么特別的特征,不好找,不好找啊。”
希望一點(diǎn)點(diǎn)被磨滅。陳陽(yáng)勸我:“要不,就算了吧。也許爸只是懷念一段青春,沒什么特別的。我們別自己嚇自己。”
我搖搖頭,指著照片上父親的眼睛,“你看他的眼神,那不是懷念青春,那是……把什么東西丟在那兒了。”
那天晚上,我們?nèi)チ艘患耶?dāng)?shù)厝送扑]的館子吃大盤雞。鄰桌坐著幾個(gè)本地的老人,喝著“奪命大烏蘇”,用我們聽不懂的維吾爾語(yǔ)高聲談笑。我沒什么胃口,心里堵得慌。
陳陽(yáng)一直在給我夾菜,“吃點(diǎn)吧,你都兩天沒好好吃飯了。”
我剛拿起筷子,就聽到鄰桌一個(gè)老人用帶著口音的普通話說(shuō)了一句:“……那時(shí)候我們還在溫宿的林場(chǎng),跟上海來(lái)的知青一起……”
我猛地抬起頭,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樣,拿著手機(jī)就走了過去。
“大爺,不好意思,打擾一下。”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(lái)不那么顫抖,“您剛才說(shuō)……您認(rèn)識(shí)上海來(lái)的知青?”
老人醉眼惺忪地看著我,又看看我手機(jī)上的照片。他身邊一個(gè)稍微年輕點(diǎn)的男人,應(yīng)該是他兒子,用維吾爾語(yǔ)跟他解釋著什么。
老人瞇著眼睛,看了很久很久,久到我以為他又要搖頭。
突然,他指著照片的背景,那片金色的胡楊林,很肯定地說(shuō):“這個(gè)地方,我知道。不是市里,在塔里木河邊上,我們叫它‘倒影林’。那里的胡楊樹,都長(zhǎng)在水邊上,天一藍(lán),水里全是胡楊的影子,好看得很。”
我的心跳瞬間加速。“那……那照片上的人呢?”
老人搖了搖頭,“人,我不認(rèn)識(shí)。但是,我知道那時(shí)候三大隊(duì)確實(shí)有個(gè)上海來(lái)的技術(shù)員,姓李,是來(lái)教我們種棉花的。后來(lái)……好像是家里出了事,急匆匆就回去了。”
姓李的技術(shù)員。
我手心全是汗,追問道:“大爺,那您說(shuō)的那個(gè)‘倒影林’,現(xiàn)在還在嗎?怎么去?”
“在,怎么不在。胡楊一千年不死,死了一千年不倒,倒了一千年不朽。”老人喝了口酒,豪邁地說(shuō),“你們往阿瓦提方向開,過了柯柯牙,再往沙漠里走,看到河就到了。不過現(xiàn)在天冷,沒什么人去。”
那一晚,我終于睡了個(gè)好覺。我夢(mèng)見了父親,他還是照片里年輕的模樣,站在一片金色的胡楊林里,對(duì)著我笑。
第二天一早,我們租了一輛越野車,按照老人的指點(diǎn),向著塔里木河的方向開去。
車子駛出市區(qū),窗外的景色越來(lái)越荒涼。城市的水泥森林被一望無(wú)際的戈壁取代,偶爾有幾叢紅柳和駱駝刺頑強(qiáng)地生長(zhǎng)著。天與地在地平線上連成一條筆直的線,那種遼闊和蒼茫,讓人的心也跟著空曠起來(lái)。
陳陽(yáng)握著方向盤,輕聲說(shuō):“爸當(dāng)年,就是每天看著這樣的景色嗎?”
我沒有回答。我只是在想,一個(gè)在江南水鄉(xiāng)長(zhǎng)大的年輕人,是懷著怎樣的心情,來(lái)到這個(gè)與故鄉(xiāng)截然不同的世界?又是怎樣的經(jīng)歷,讓他把一部分靈魂永遠(yuǎn)地留在了這里?
車子在顛簸的土路上行駛了近三個(gè)小時(shí),我們終于看到了一條河。河水并不寬闊,但在干旱的戈壁上,已然是生命的奇跡。河岸上,果然矗立著一片形態(tài)各異的胡楊林。
冬日的胡楊,葉子早已落盡,只剩下遒勁滄桑的枝干,伸向湛藍(lán)的天空。它們有的如盤龍,有的似臥虎,每一棵都像一座凝固的雕塑,無(wú)聲地訴說(shuō)著千年的故事。
我們下了車,沿著河岸慢慢走。這里太安靜了,只有風(fēng)聲和我們腳踩在枯葉上的沙沙聲。我拿出手機(jī),對(duì)比著照片里的背景。
“是這里,”我指著遠(yuǎn)處一棵造型奇特的胡大楊樹,“你看,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樣。”
我們找到了那個(gè)精確的地點(diǎn)。我站在父親當(dāng)年站過的位置,模仿著他的姿勢(shì),讓陳陽(yáng)給我拍了張照片。按下快門的瞬間,我突然有一種時(shí)空交錯(cuò)的錯(cuò)覺,仿佛能看到五十年前,那個(gè)年輕的上海知青,和那個(gè)美麗的維吾爾族姑娘,就站在這里,笑靨如花。
附近有一個(gè)小小的村落,稀稀拉拉的十幾戶人家,土坯房,院子里曬著紅色的辣椒和黃色的玉米。我們想去碰碰運(yùn)氣,看有沒有人還記得當(dāng)年的事。
村口坐著幾個(gè)曬太陽(yáng)的老人,看到我們兩個(gè)外來(lái)者,眼神里充滿了好奇。
我鼓起勇氣,走上前,拿出手機(jī)。
一位滿臉皺紋的阿帕(維吾爾語(yǔ),意為奶奶)接過了我的手機(jī)。她身邊的人都湊了過來(lái),嘰里呱啦地討論著。
突然,那位阿帕的眼睛亮了。她指著照片上的姑娘,激動(dòng)地說(shuō)了一長(zhǎng)串維吾爾語(yǔ)。她身邊一個(gè)年輕人給我們翻譯:“我奶奶說(shuō),她認(rèn)識(shí)!這是阿依古麗!是她小時(shí)候的鄰居!”
阿依古麗。
我心里默念著這個(gè)名字,眼眶一熱,差點(diǎn)掉下淚來(lái)。終于,不再是一個(gè)虛無(wú)的影子,她有了一個(gè)如此美麗的名字。
“那……那她現(xiàn)在在哪里?”我急切地問。
年輕人的表情變得有些為難,他和奶奶又交流了幾句,然后對(duì)我們說(shuō):“阿依古麗阿帕……她很多年前就嫁人了,嫁到了柯柯牙那邊。聽說(shuō),她丈夫前幾年去世了,現(xiàn)在跟著她兒子一起過。”
他頓了頓,眼神有些閃爍,補(bǔ)充道:“她……她有個(gè)兒子……”
這句話他說(shuō)得很慢,而且沒有說(shuō)完,只是嘆了口氣,搖了搖頭。
這沒說(shuō)完的半句話,像一根刺,瞬間扎進(jìn)了我的心里。一個(gè)不祥的預(yù)感,讓我手腳冰涼。
【大轉(zhuǎn)折:找到關(guān)鍵人物線索,并埋下關(guān)于“兒子”的巨大懸念】
回去的路上,我和陳陽(yáng)一路無(wú)話。車?yán)锏呐瘹忾_得很足,我卻覺得渾身發(fā)冷。那個(gè)年輕人欲言又止的表情,那句沒說(shuō)完的話,在我腦海里反復(fù)回響。
“她有個(gè)兒子……”
這背后藏著什么?一個(gè)我不敢深思的答案,像一頭蟄伏的猛獸,即將破籠而出。
晚上,我做了一個(gè)夢(mèng)。夢(mèng)里,我走在胡楊林里,父親在前面不停地走,我怎么追也追不上。我大聲喊他,他回過頭,臉上卻是我母親的表情,哀傷又決絕。
柯柯牙,離我們住的地方不遠(yuǎn)。那里是阿克蘇的綠色屏障,一片人工種植的浩瀚林海,創(chuàng)造了沙漠變綠洲的奇跡。第二天,我們驅(qū)車前往。
根據(jù)村里人提供的模糊信息,我們?cè)诳驴卵梨?zhèn)附近打聽了很久,終于找到了阿依古麗的家。那是一個(gè)被葡萄藤架包圍的小院,院門虛掩著。
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手心里的汗把手機(jī)都浸濕了。陳陽(yáng)握住我的手,給了我一個(gè)鼓勵(lì)的眼神。
我深吸一口氣,推開了院門。
院子里,一個(gè)身穿民族服飾的女人正在晾曬被子。她已經(jīng)不再年輕,歲月在她臉上刻下了深深的淺淺的紋路,但那雙眼睛,依然像我照片上看到的那樣,清澈,沉靜。
她就是阿依古麗。
她看到我們,并沒有很驚訝,只是停下了手里的活,平靜地看著我們。
我走上前,聲音有些發(fā)顫:“您好……我們是從上海來(lái)的。”
我把手機(jī)遞給她,屏幕上是那張我和父親在胡楊林里的合影,旁邊,是我特意放上的那張老照片。
她的目光落在老照片上,久久沒有移開。她的手微微顫抖著,伸出來(lái),想要觸摸屏幕,卻又在半空中停住。
良久,她抬起頭,看著我,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話說(shuō):“進(jìn)來(lái)……喝杯茶吧。”
我無(wú)法形容那一刻的心情。我曾想象過無(wú)數(shù)種見面的場(chǎng)景,或激動(dòng),或怨恨,或淚流滿面。但都不是這樣。她平靜得像一潭深水,將所有的波瀾都藏在了水底。
我們走進(jìn)屋里,典型的維吾爾族民居,墻上掛著毯子,地上鋪著地毯。她給我們倒了熱奶茶,放了很多糖。
沉默。漫長(zhǎng)的沉默。
最后,還是我先開了口:“我父親……他叫李建國(guó)。他上個(gè)月,去世了。”
阿依古麗端著茶杯的手,幾不可查地抖了一下。她沒有看我,只是低著頭,輕聲說(shuō):“他……是個(gè)好人。”
和我母親一模一樣的話。
從兩個(gè)深愛同一個(gè)男人的女人嘴里說(shuō)出來(lái),這句話的分量,重得讓我喘不過氣。
“我們整理他的遺物時(shí),發(fā)現(xiàn)了這個(gè)。”我把那張老照片的實(shí)體拿了出來(lái)。
她終于伸出手,接過了照片。她的指腹輕輕摩挲著照片上父親年輕的臉龐,眼神里流露出無(wú)盡的懷念與哀傷。
“那時(shí)候,我們都年輕。”她開口了,像是在對(duì)我說(shuō)話,又像是在自言自語(yǔ)。
她的故事,像一幅褪色的畫卷,在我面前緩緩展開。
他們相識(shí)于棉花試驗(yàn)田,他是來(lái)支邊的技術(shù)員,她是公社里最勤勞的姑娘。他教她科學(xué)種植,她教他說(shuō)維吾爾語(yǔ)。在廣袤的天地和金色的胡楊林里,兩個(gè)年輕人相愛了。那是一種不含任何雜質(zhì)的,純粹的愛情。
“他說(shuō),等他完成任務(wù),就向組織申請(qǐng),留在這里,和我結(jié)婚。”阿依古olie的眼眶紅了,“我們連以后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,如果是男孩,就叫‘托乎提’,是‘留下’的意思。”
“那后來(lái)呢?”我追問。
“后來(lái)……他接到一封電報(bào),說(shuō)他父親病危,讓他立刻回去。他走的時(shí)候,跟我說(shuō),他最多一個(gè)月就回來(lái)。他把這塊手表留給了我,說(shuō)等他回來(lái),就用一塊上海牌的新手表?yè)Q回去。”她卷起袖子,手腕上,是一塊老舊的,早已停止走動(dòng)的男士手表。表盤已經(jīng)磨損得看不清刻度。
“他再也沒有回來(lái)。”她的聲音很輕,卻像一把重錘,敲在我的心上。“我等了他一年,兩年……給他寫信,都石沉大海。后來(lái),公社的領(lǐng)導(dǎo)告訴我,他在上海結(jié)婚了。”
我的喉嚨像是被什么堵住了,一個(gè)字也說(shuō)不出來(lái)。我知道,那不是父親的本意。我聽母親說(shuō)過,爺爺當(dāng)年病重,臨終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父親成家。那是一場(chǎng)被親情和孝道“綁架”的婚姻。父親反抗過,但最終還是屈服了。
“我不信。”阿依古麗搖著頭,淚水終于滑落,“我不信他會(huì)騙我。后來(lái)我才知道,我家里人把他寫給我的信都燒了。他們不想我嫁給一個(gè)漢族,一個(gè)隨時(shí)都可能走的人。”
命運(yùn)的陰差陽(yáng)錯(cuò),造成了三個(gè)人的終身遺憾。
我看著眼前這個(gè)為我父親蹉跎了歲月的女人,心里五味雜陳。我不知道該說(shuō)什么,任何安慰的語(yǔ)言,在這樣沉重的人生面前,都顯得蒼白無(wú)力。
我深吸一口氣,問出了那個(gè)盤旋在我心里,最讓我恐懼的問題。
“那個(gè)村里的人說(shuō)……您有一個(gè)兒子……”
阿依古olie的身體僵住了。她背過身去,擦了擦眼淚,沉默了很久。
“他叫圖爾蓀。”她終于開口,聲音里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,“是個(gè)好孩子,現(xiàn)在是柯柯牙的護(hù)林員,就在這片林子里工作。”
她沒有說(shuō)圖爾蓀的父親是誰(shuí)。
她不必說(shuō)。
【扎心金句】她轉(zhuǎn)過頭,看著窗外那片無(wú)盡的綠色,輕聲說(shuō):“有些事,說(shuō)清楚了,也就臟了。不說(shuō),放在心里,還能開出一朵干凈的花。”
就在這時(shí),屋子的門被推開了。
一個(gè)身材高大,皮膚黝M的男人走了進(jìn)來(lái)。他大約五十歲左右,穿著一身迷彩服,肩上還落著幾片葉子。他看到我們,愣了一下,隨即露出憨厚的笑容。
“阿帕,來(lái)客人了?”他用維吾爾語(yǔ)問道。
然后,他轉(zhuǎn)向我們,用普通話打招呼:“你們好。”
在他抬起頭的一瞬間,我如遭雷擊。
那雙眼睛。
那雙深邃、沉靜,帶著一絲憂郁的眼睛,和我父親,一模一樣。
【大轉(zhuǎn)折:那個(gè)只存在于猜測(cè)中的“兒子”活生生地出現(xiàn)在眼前】
時(shí)間仿佛在那一刻靜止了。
我呆呆地看著他,大腦一片空白。陳陽(yáng)在我身后,緊緊握住了我的胳膊,我能感覺到他的手心也在出汗。
“這是圖爾蓀,我兒子。”阿依古麗為我們介紹,語(yǔ)氣盡量顯得自然。“圖爾蓀,這兩位是……從上海來(lái)的客人,是你李叔叔的……”她卡住了,不知道該用什么詞來(lái)形容我們的關(guān)系。
“我是他的女兒。”我聽見自己的聲音說(shuō),干澀而陌生。
圖爾蓀臉上的笑容凝固了。他看著我,又看看他母親,眼神里充滿了困惑。“李叔叔?哪個(gè)李叔叔?”
“就是……年輕時(shí)候,和你阿帕一起工作的那個(gè)上海知青。”阿依古麗艱難地解釋著。
圖爾蓀的表情變得復(fù)雜起來(lái)。他顯然聽說(shuō)過這個(gè)名字,但似乎并不知道更深層的故事。他沉默了片刻,然后對(duì)我伸出手:“你好。我叫圖爾蓀。”
他的手掌寬大而粗糙,布滿了老繭,握手的時(shí)候很有力。我能感覺到,這是一個(gè)常年與土地和樹木打交道的人。
我有一個(gè)哥哥。
這個(gè)念頭毫無(wú)征兆地闖進(jìn)我的腦海,讓我的心臟一陣緊縮。一個(gè)我素未謀面,血脈相連的哥哥。
那天中午,阿依古olie堅(jiān)持留我們吃飯。她做了一大桌子豐盛的飯菜,手抓飯,烤包子,還有清燉羊肉。飯桌上的氣氛很詭異,每個(gè)人都心事重重,卻又假裝若無(wú)其事。
圖爾蓀話不多,但很熱情。他不停地給我們夾菜,給我們講柯柯牙的故事,講他如何帶著工人們一代代地植樹,如何把一片荒漠變成綠洲。他說(shuō)話的時(shí)候,眼睛里閃著光,那是一種發(fā)自內(nèi)心的,對(duì)腳下這片土地的熱愛。
我看著他,仿佛看到了父親的另一面。我的父親,一輩子在圖紙和數(shù)據(jù)里打轉(zhuǎn),嚴(yán)謹(jǐn)而壓抑。而眼前的這個(gè)男人,他的生命和那些胡楊一樣,粗糲,堅(jiān)韌,充滿了原始的生命力。
【共情觸發(fā)器:一個(gè)從未見過的親人,身上卻有著父親的影子】
飯后,圖爾蓀的女兒,一個(gè)七八歲的小姑娘放學(xué)回來(lái)了。她叫古麗米熱,意思是“像花兒一樣的希望”。小姑娘很害羞,躲在爸爸身后,偷偷地看我們。
阿依古olie把她拉到身前,讓她叫我們“叔叔”“阿姨”。
小姑娘看著我,突然用維吾爾語(yǔ)問了一句什么。
圖爾蓀笑了,翻譯給我們聽:“她問,阿姨你的眼睛,為什么和阿公(爺爺)的那么像?”
我的心,被狠狠地刺了一下。我強(qiáng)忍著淚水,對(duì)小姑娘笑了笑,從包里拿出一塊巧克力遞給她。
那一刻,我突然感到一種奇異的溫情。在這個(gè)遙遠(yuǎn)的小院里,我和一個(gè)陌生的家庭,因?yàn)橐粋€(gè)共同的男人,被一條看不見的線給連接了起來(lái)。這里有我同父異母的哥哥,有我從未謀面的侄女。他們過著我完全不了解的生活,卻和我流著一樣的血。
【溫情炸彈:在最復(fù)雜的局面中,孩子的一句童言無(wú)忌帶來(lái)的情感沖擊】
下午,圖爾蓀要上山巡林,他問我們要不要一起去看看。
我和陳陽(yáng)答應(yīng)了。
我們坐著他的那輛破舊的皮卡車,在林區(qū)里穿行。圖爾蓀指著窗外一排排挺拔的白楊,自豪地說(shuō):“這些,都是我們親手種下的。剛來(lái)的時(shí)候,這里全是沙子,風(fēng)一吹,眼睛都睜不開。現(xiàn)在你看,跟公園一樣。”
我問他:“你一直生活在這里嗎?沒想過去外面看看?”
他笑了,露出一口白牙。“外面?上海嗎?想過。年輕的時(shí)候,總聽我阿帕念叨上海。她說(shuō)那里有高樓大廈,有黃浦江。但是,我離不開這里。我的根在這里。”
他的根在這里。我父親的根,又在哪里呢?
我們?cè)谝惶幐叩赝O隆倪@里望下去,整片柯柯牙林海盡收眼底,綠色的波濤一直延伸到天際。遠(yuǎn)處,是巍峨的天山雪峰。
圖爾蓀從地上撿起一塊石頭,遞給我。“這是胡楊木的化石。這片土地下面,埋著很多。帶回去做個(gè)紀(jì)念吧,千年不朽。”
我接過那塊沉甸甸的化石,心里也沉甸甸的。
那天晚上,我給母親打了個(gè)電話。響了很久,她才接。
“喂?”
“媽,是我。”
“嗯。”
我不知道該說(shuō)什么,千言萬(wàn)語(yǔ)堵在喉嚨口。我見到他了?我有個(gè)哥哥?這些話,我一個(gè)字也說(shuō)不出口。
我只能說(shuō):“媽,我……我看到了一片很美的胡楊林。”
電話那頭,是長(zhǎng)久的沉默。久到我以為她已經(jīng)掛了。
然后,我聽到她帶著濃重鼻音的聲音,她說(shuō):“小冉,早點(diǎn)回來(lái)吧。家里的湯,都給你燉好了。”
掛掉電話,我再也忍不住,蹲在酒店房間的窗邊,看著窗外的陌生城市,泣不成聲。
【沉默的力量:母女之間心照不宣的對(duì)話,勝過千言萬(wàn)語(yǔ)】
我和陳陽(yáng)在阿克蘇多停留了兩天。
這兩天,我心里一直在進(jìn)行著天人交戰(zhàn)。
要不要告訴圖爾蓀真相?
告訴他,他的人生,他的身份,都建立在一個(gè)被隱瞞了五十年的故事之上。告訴他,他有一個(gè)從未見過面,已經(jīng)去世的父親,在遙遠(yuǎn)的上海,還有一個(gè)同父異母的妹妹。
這太殘忍了。
這會(huì)打破阿依古麗用一生維護(hù)的平靜,會(huì)給圖爾蓀原本簡(jiǎn)單純粹的世界投下一顆炸彈。他會(huì)如何看待自己的母親?如何看待那個(gè)素未謀面的“父親”?
可是,他有權(quán)利知道真相,不是嗎?
我把我的糾結(jié)告訴了陳陽(yáng)。
他抱著我,輕輕拍著我的背。“小冉,我們先想一個(gè)問題。你揭開這個(gè)傷疤,是為了誰(shuí)?是為了你自己心里的一個(gè)答案,還是真的為了他們好?”
我愣住了。
他繼續(xù)說(shuō):“爸一輩子都沒有說(shuō),阿依古麗阿帕一輩子也沒有說(shuō)。他們兩個(gè)當(dāng)事人,都選擇了沉默。這個(gè)秘密,是屬于他們那個(gè)年代的。也許,沉默,就是我爸對(duì)他們母子倆,最后的保護(hù)。”
“他不是不負(fù)責(zé)任,他可能……是不知道該怎么負(fù)責(zé)任。回去,還是留下,對(duì)他來(lái)說(shuō),都是撕心裂肺的選擇。他選了孝道,選了我們,就注定要虧欠這里。”
【關(guān)鍵轉(zhuǎn)折:丈夫的一番話,讓敘述者開始重新思考“真相”的意義】
我突然想起了父親臨終前的情景。
他躺在病床上,已經(jīng)有些神志不清。他拉著我的手,嘴里反復(fù)念叨著一個(gè)模糊的詞。我當(dāng)時(shí)聽不清,以為是胡話。現(xiàn)在我才明白,他念的是“阿依古麗”。
他最后對(duì)我說(shuō)的話是:“小冉,爸這輩子……對(duì)不住……”
他沒有說(shuō)完。我一直以為,他是對(duì)我和母親感到虧欠,虧欠他不夠熱情,不夠體貼。
現(xiàn)在我懂了。他這句話,是對(duì)所有人說(shuō)的。對(duì)母親,對(duì)他遠(yuǎn)在天邊的愛人,和他那個(gè)從未謀面的兒子。
【倒敘插敘:在做出關(guān)鍵決定前,插入臨終回憶,讓情感和動(dòng)機(jī)更立體】
我父親的沉默,不是冷漠,而是他背負(fù)了一生的十字架。他把所有的痛苦、掙扎和思念,都鎖在了那個(gè)錫皮盒子里,鎖在了心里。
他的這個(gè)“缺陷”,他一生的沉默,最終把我引向了這里。不是為了審判,而是為了理解。
我決定了。
我要把這個(gè)秘密,像父親一樣,帶回屬于它的地方。
真相有時(shí)候,并不是解藥,而是毒藥。而善良,是選擇不把這毒藥遞給別人。
臨走的前一天,我們?nèi)ズ桶⒁拦披惸缸痈鎰e。
我沒有說(shuō)任何關(guān)于身世的話題。我們就像普通的,來(lái)自父親故鄉(xiāng)的晚輩,來(lái)探望一位長(zhǎng)輩。
阿依古麗好像也松了一口氣。她從房間里拿出一個(gè)小小的,手工編織的掛毯,圖案是金色的胡楊林。
她把掛毯交到我手里,說(shuō):“這個(gè),你帶回去。替我……放在他的墳前吧。”
她沒有說(shuō)“李建國(guó)”,只說(shuō)“他”。我們都懂。
圖爾蓀也來(lái)了。他開著他那輛皮卡,送我們?nèi)C(jī)場(chǎng)。路上,他還是像之前一樣,給我們講林場(chǎng)的故事,講他女兒的趣事。
在機(jī)場(chǎng)告別時(shí),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個(gè)用布包著的東西,遞給我。“這個(gè),是我自己雕的。”
我打開一看,是一塊胡楊木,被雕刻成一片葉子的形狀,紋理清晰,質(zhì)感溫潤(rùn)。
“我聽阿帕說(shuō),李叔叔是南方人。南方的樹葉,是不是都長(zhǎng)這樣?”他憨厚地笑著。
我握著那片木葉,感覺它烙在我的掌心,滾燙。我點(diǎn)點(diǎn)頭,說(shuō)不出話。
“常回來(lái)看看。”他說(shuō)。
“好。”我答應(yīng)他。
飛機(jī)起飛的時(shí)候,我從舷窗望下去。那片創(chuàng)造了奇跡的綠色,在蒼茫的戈壁上,顯得如此倔強(qiáng),又如此溫柔。
我突然明白了,為什么建議人們“不要隨便去阿克蘇”。
因?yàn)槟憧赡軙?huì)在那里,看到人性的另一面。看到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下,那些被忽略的,個(gè)體的愛與哀愁。看到沉默背后,可能藏著雷霆萬(wàn)鈞。看到一生的虧欠,也可以是另一種形式的成全。
回到上海,是一個(gè)陰雨天。濕冷的空氣,與阿克蘇的干冽截然不同。
我去了父親的墓地。
母親也來(lái)了。她撐著一把黑色的傘,站在我身邊。
我把阿依古麗給我的那個(gè)小掛毯,輕輕地放在了墓碑前。金色的胡楊林,在灰色的石碑上,顯得格外醒目。
母親看著那個(gè)掛毯,看了很久。
雨絲落在傘面上,發(fā)出沙沙的聲響。
“你都……知道了?”她終于開口,聲音很輕,像是怕驚擾了誰(shuí)。
“嗯。”
“她……還好嗎?”
“挺好的。兒子很孝順,孫女也可愛。”
母親點(diǎn)了點(diǎn)頭,沒再說(shuō)話。她從自己的口袋里,也拿出了一個(gè)東西。那是一封信,信紙已經(jīng)黃脆,折痕處幾乎要斷裂。
“這是你爸當(dāng)年從新疆回來(lái)后,我們結(jié)婚前,寫給我的。”
我接過來(lái),顫抖著打開。
信里,父親用他那嚴(yán)謹(jǐn)工整的字跡,坦白了他和阿依古麗的一切。他說(shuō),他心里有愧,他給不了她一個(gè)完整的,沒有陰影的婚姻。他在信的最后說(shuō),如果她不能接受,他愿意取消婚約,承擔(dān)一切后果。
我的眼淚,一瞬間決堤。
我看著母親,她平靜地看著遠(yuǎn)方,說(shuō):“我選擇了嫁給他。”
“為什么?”我哽咽著問。
【扎心金句】母親淡淡地說(shuō):“一輩子很長(zhǎng),不能只盯著一個(gè)坎兒過。一輩子也很短,能陪著走一段,就不錯(cuò)了。”
她收回目光,看著我,伸手擦掉我臉上的淚水。“你爸這輩子,心里苦。我不想他更苦。”
【價(jià)值觀的藝術(shù)化表達(dá):不說(shuō)教,讓人物的選擇和一句樸素的話,詮釋一生的智慧和善良】
那一刻,我終于徹底理解了我的母親。她的隱忍,不是軟弱,而是一種更深沉的愛與慈悲。她用一生的時(shí)間,去守護(hù)一個(gè)男人的尊嚴(yán),和另一個(gè)家庭的安寧。
我們離開墓園的時(shí)候,雨停了。太陽(yáng)從云層里掙扎出來(lái),在濕漉漉的地面上,投下斑駁的光影。
我手里緊緊握著圖爾蓀送我的那片胡楊木葉,另一只手,被陳陽(yáng)溫暖地牽著。母親走在我們身邊,步履比來(lái)時(shí),似乎輕松了一些。
我想,我終于知道了那些“去阿克蘇之前必須知道的事”。
那不是風(fēng)景,不是美食。
而是關(guān)于選擇,關(guān)于承擔(dān),關(guān)于沉默,和關(guān)于愛。
是關(guān)于,一個(gè)看似平凡的家庭,如何在時(shí)代洪流和命運(yùn)的交錯(cuò)中,用各自的方式,守護(hù)著彼此,也成全了遠(yuǎn)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