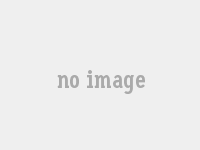登基大典百官高呼萬歲溥儀嚇哭,載灃脫口而出就快完了,不料應驗
1912年初,一道退位詔書自紫禁城傳出。大清王朝覆滅了。之前的一切,只用“就快完了”幾字就讓人有點哭笑不得。誰想得到,那一句臨時脫口的嘟囔,竟成最后的注腳。

北京的冬天比想象揮之不去。光緒崩逝的時候,城里還是陰霾一片。宮門緊閉,檐角掛著冰,消息鉆著縫流向各家各戶。載灃蹲在慈禧垂簾幃幕后,心里亂成一鍋粥。他本就無心政務,少年時膽小懦弱,眼下竟輪到把自己的兒子往權力漩渦里推,這誰也料不到。
慈禧盤桓在屏風后,還是像往常那樣,氣場壓得殿里幾乎沒人敢抬頭。她低聲說“這是神意,列祖列宗前已卜卦——準。”靜極而生蔓延。載灃發愣,低聲自語:“溥儀才三歲……三歲的,真的能當皇帝嗎?”
外面風聲走漏,醇王府立刻掀鍋。溥儀的祖母,還沒等懿旨讀完便昏厥過去。等清醒,卻還是抓著孫子鼻涕眼淚齊下,抱緊不撒手。她幼年就見慣宮斗,早識慈禧手段,家里頭的人都知道她脾氣倔得很。這會兒哭著喊:“你們把自己的娃弄死了,現在又要來禍害我的,這可不行!”
她的執拗沒有用,噩耗壓下來。內監進府抱人,溥儀被陌生人又拉又扯,小胳膊小腿亂揮亂踢,哪里懂宮廷規矩?“諭旨不可違”的道理,在嗷嗷哭鬧的孩子眼里沒有分量。太監們一番合計,終于由載灃自己抱著“皇帝”,一路把孩子、乳母,還有哭天搶地的祖母攙出來,蹭著將人帶進紫禁城。天還沒亮,三歲的溥儀就這樣被送到這座“龍椅”前——儀式開始。
清晨,紫禁城里安靜得能聽見呼吸。銀霧、微光、鼓樂,官員按次序跪滿丹墀,個個頭磕得叭叭響。殿里密密麻麻的臣子,山崩地裂的鑼鼓、鼓聲、金鐘,烘托得氣氛逼仄——沒人注意角落里溥儀的神情。他坐在龍椅上,臉上淚痕還沒擦干,只覺得這陣勢嚇人。哪來的悲壯,明明就是害怕。
“萬歲!萬歲!萬萬歲!”百官高呼,似乎喊到嗓子劈裂。沒見過大場面的孩子哪里受得了?于是,哭聲和鑼聲交雜成一鍋,場面突然尷尬。載灃臉上掛不住了,本來就膽小,急得心慌手亂,在人前當眾失態,一句“快完了!就快完了!一完就回老家!”脫口而出,聲音不小,底下人都聽見了。
文武百官雖沒法多嘴,私下里早已互相揣測:“他說‘快完了’,啥意思?”滿漢官員當場竊竊私語,有人甚至懷疑是不是這場面,注定沒法再撐太久。其實清朝自咸豐以后已積重難返,中國變局箭在弦上,宮廷里外皆想著自保,載灃那點失控,反倒顯出某種真實。
不上心的父親,稚嫩的皇帝,臨死前勉力支撐的老太太。朝代的末路,從宮門到街頭,人人都能嗅出一絲苦澀荒誕。慈禧太后第二天便病死,像是拎著一件甩手包袱就撒手離去,誰還關心小皇帝掙扎哭鬧?這樣的登基,怎么看也有種兒戲的味道。
外人的眼睛里是冠冕堂皇的儀式,可宮里的慌亂只怕比外面更多。養心殿里聞不到半點磅礴氣象,只剩一堆東倒西歪的爭吵、恐懼與不甘,雞鳴狗盜之氣徹底彌散。皇權這東西,有時候強撐的時間長了,反而看不清何時才是盡頭。誰剛登基三年就被時代扔下井溝?溥儀偏就趕上了。
1911年,轟動全球的辛亥革命到來。全國多地起義,呼聲日急。新軍、官紳、商賈對老體制早已不耐,朝廷上下都覺這桿大旗撐不住。溥儀其實什么都不懂,他還在宮墻內,周圍人說得最多的還是安慰,“沒事,皇上還小,不必擔心。”可大廈將傾,個人努力全都像笑話。一紙退位詔書,隆裕太后只得代為簽字。末代皇帝沒能說什么,甚至不知發生了什么。
很多人都說清王朝就是亡于時代洪流,可也有不同的看法——可能就是父親一句“快完了”問心有愧,或者說,注定大清江山誰也背不動。三歲的溥儀,如果不是趕上腥風血雨,只是平常人家,他爹可能還會擔心晚飯以后他睡不著覺。
這段歷史里找不到毅力奮斗,也沒有跌宕起伏的逆轉,反倒全都是意外和無奈。可偏偏這樣的真相,讓人覺得荒謬里帶著幾分心酸。頭上金冠、身下龍椅,終究抵不過冷清的墻角和一張蜷縮的小臉。
誰能想到,三歲的孩子和王朝的末世,兩條線正好交匯,勉強支撐的人間大戲就此落幕?誰又能說,當年那句不合宜的嘟囔真是神來之筆?人心的變化,時代的選擇,百年之后再看,依舊說不清。
其實這么說不完全公允。清末不少官員明明對時局并非全無認知,不少人也曾嘗試自保,聯絡革命黨或暗中謀生退路。歷史表面安靜,底層卻搏動著波瀾,宮廷密道里暗流涌動。可惜終究還是落得無聲無息。“一完就回老家”,也沒回得成。
清宮規矩講究天命,但真到了末日,哪還分得清是神意還是無意?溥儀后來回憶幼年,并無帝王自覺,只有奶媽、祖母和一群陌生太監。大清帝國的最后時刻,剪不斷的荒唐。民國建立初,紫禁城里還是舊貌,可宮外新政轟轟烈烈,那道退位詔書成了歷史僅剩的聲音。
外面雪化了,滿城的泥水都泛著冷亮。街頭巷尾議論紛紛。宮里依舊每日按時打鐘點,紫禁城關門的聲音聽上去格外悶。溥儀哭過一場又一場,偶爾還是玩耍捉迷藏。大臣們或遠走他鄉或混入新政府,誰也顧不得勸慰——反正都快完了,干脆別太較真。
王朝的更替被幾句唬人的吉兇摘了頭,結局之草率,讓人忍不住側目。究竟是溥儀沒命?大清本該完?還是每一個浸在權力網絡里的人都只是趕路的路人?人們翻出史料細看,仍能找到無數矛盾,不少宮人信誓旦旦說“其實可以保住”,可歷史卻不曾給改正的機會。就像當初載灃的無心之言,既是泄氣,也成了預言。
“就快完了。”這句話在那些年間,不只是一個父親的口頭禪,它幾乎成了消散王朝最后的回響。
幾個人物,幾句對白,帶著觀世的距感在大幕落下后徹底無聲。浮世縱橫,誰會想一個三歲的男孩被動地成了帝國落幕的象征?有人說歷史偶然,有人信命定——有些事,到最后本來就說不清道不明。
人間百態終究輪回。皇帝落淚,大臣退散,皇朝覆滅。**就這樣,一切都過去了。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