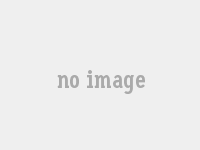玄學:太歲壓祭主禁忌,喪事回避法則,犯者百日損運!
殘陽如血,將西山村口那棵老槐樹的枯枝染得紅透,仿佛枝椏間都在滴著血珠。王二麻子縮著脖子,佝僂著背,一步三挪地往村外蹭。他懷里揣著的紙錢被穿堂風卷得嘩嘩作響,像是有無數只小手在拉扯。剛給亡母燒了頭七紙,他卻總覺后頸涼颼颼的,那股涼意不似秋風,倒像有人對著脖子不住地吹冷氣,順著衣領往里鉆,凍得骨頭縫都發疼。
“喪家過處,三避太歲方為吉。” 村口瞎眼的張半仙常坐在磨盤上念叨這話,他那雙渾濁的眼珠望著天,聲音里帶著說不清的敬畏。王二麻子此刻腦門上沁出冷汗,才猛然想起,今早出殯時,抬棺的八個壯漢不知是被誰指引,竟踩著太歲方位走了整整三里地。當時他只顧著哭喪,壓根沒留意這些,如今想來,張半仙說過的 “太歲頭上動土,不出百日必有禍” 像根針,狠狠扎進他心里。
一陣旋風毫無征兆地卷起地上的紙灰,在他腳邊盤旋成個黑圈,那圈邊緣整齊,像是用墨線畫過一般。王二麻子腿一軟,“噗通” 一聲癱在地上,褲腿被冷汗浸透。他眼睜睜看著那圈紙灰順著褲腳往上爬,所過之處,褲子瞬間變得焦黑。他想喊,喉嚨卻像被堵住,只能發出嗬嗬的怪響 —— 這年冬月,西山村凍死的第三個人,正是他。而前兩個,都是上個月參與過一場沖犯太歲的喪事的幫工。

歐陽上機蹲在青石板鋪就的巷口,指尖捻著三枚銹跡斑斑的銅錢。銅綠斑駁的錢面凹凸不平,映出他清瘦的臉。他眉骨高突,眼窩陷得像兩口深井,唯有眼珠轉動時,才泄出幾分精光,像是藏在暗夜里的星辰。
“歐陽先生,這陰宅當真不能動?” 糧商趙德發搓著雙手,他那身錦緞袍子上的盤扣被蹭得锃亮,反射著正午的日光。他想遷祖墳的事,在青溪鎮已傳了半月,鎮上人都知道他相中了城南那塊據說埋著前朝太傅的寶地。
歐陽上機將銅錢擲在龜甲里,“叮當” 脆響驚飛了檐下的麻雀,幾只麻雀撲棱著翅膀,在半空盤旋兩圈,嘰嘰喳喳地像是在警示什么。“趙老板可知,壬山丙向今年犯太歲?” 他聲音不高,卻像石子投進冰湖,激起層層漣漪,“動土便是沖了太歲爺的寶座,這可不是鬧著玩的。”
趙德發臉上的肉抖了抖,肥厚的下巴上堆起褶子。他上個月托人從鄰縣買來那塊地,光銀子就花了三百兩,心里正美滋滋地盤算著遷墳后能官運亨通。“先生是說,遷墳會出事?” 他咽了口唾沫,聲音有些發顫。
“不是會出事。” 歐陽上機撿起一枚銅錢,錢眼里透著天光,亮得有些刺眼,“是一定會出事。” 他起身時,青布長衫的下擺掃過墻角的枯草,露出藏在袖中的羅盤,那指針正微微顫動,像是不安分的心跳。
這歐陽上機原是江南人氏,三年前流落到這青溪鎮。沒人知道他的來歷,只曉得他懂些陰陽八卦、風水命理。鎮上誰家有紅白喜事,總愛請他去看看日子、定個方位。他住的那間小院在鎮子東頭,院里栽著棵老槐樹,門口掛著塊褪色的木牌,上面寫著 “歐陽堪輿” 四個瘦金體,筆力遒勁,不像尋常算命先生的手筆。
前幾日綢緞莊的李掌柜母親去世,請歐陽上機擇下葬時辰。他在李家堂屋的油燈下掐著指頭算到后半夜,油燈芯爆了三回,最后愣是讓李家人把出殯時辰往后推了兩個時辰。“卯時屬木,與逝者生辰八字相沖,犯了‘太歲壓祭主’的忌諱。” 他當時這般說,手指在黃歷上點著,“若按原時辰出殯,棺木必遇橫禍,輕則棺蓋脫落,重則傷及送葬之人。” 李家人雖半信半疑,但看他說得懇切,還是照做了。

此刻李掌柜正提著兩匹上好的云錦送來,臉上堆著笑,眼角的皺紋里都藏著感激:“歐陽先生真是神了!那天改了時辰后,出殯一路順順當當,連吹鼓手都說從未這般順利過,連過三條河都是風平浪靜的。”
歐陽上機擺擺手,沒收那云錦。“舉手之勞。” 他望著窗外,遠處的山尖隱在云霧里,像頭伏著的巨獸,“倒是李掌柜,令堂的墳前切記莫種冬青,冬青屬陰,易招邪祟,若是種了,不出三月,墳頭必生異狀。”
李掌柜連連應著,又說了些感激的話才離去。屋內只剩下歐陽上機一人,他從懷中摸出本泛黃的書,封面上寫著《宅經》二字,邊角都被翻得起了毛,紙頁脆得像枯葉。
這書是他祖父傳下來的。據說歐陽家祖上曾在欽天監當差,專司觀星定歷,后來遭人陷害才流落民間。祖父臨終前攥著他的手,枯瘦的手指幾乎嵌進他的肉里:“玄學不是騙術,是天地規律,順之則昌,逆之則亡。你要記住,看風水看的不是方位,是人心;算吉兇算的不是命數,是分寸。” 那時他才十二歲,似懂非懂地點頭,祖父的話卻像烙印刻在了心里。
正想著,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,“噔噔噔” 地踏在青石板上,帶著一股子慌張。鎮西頭的王屠戶撞進門來,手里的殺豬刀還帶著血,刀刃上的血珠滴在地上,暈開一小片暗紅。“歐陽先生!快去看看!我家那口子…… 那口子怕是不行了!”
歐陽上機眉頭一皺。王屠戶的妻子三天前剛生了個大胖小子,前天他還去喝了滿月酒,當時產婦氣色尚可,怎么突然就不行了?他抓起羅盤跟著王屠戶往外走,街上的行人見了王屠戶這模樣,都紛紛避讓,有人還往地上吐唾沫,覺得沾了晦氣。
“前兒個孩子辦滿月酒,請了隔壁村的張婆子來給孩子算命。” 王屠戶喘著粗氣,脖子上的青筋暴起,“張婆子說孩子命硬,八字帶煞,得找個屬虎的干爹沖沖煞氣,我就請了劉木匠來。誰知昨天起,我婆娘就上吐下瀉,今早竟人事不省了!”
歐陽上機腳步一頓。屬虎的干爹?他掐指一算,今年是辰年,虎辰相沖,這哪里是沖煞氣,分明是引煞進門。張婆子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,誤人性命。

到了王屠戶家,一股濃烈的草藥味撲面而來,混雜著血腥味,聞著讓人作嘔。產婦躺在床上,臉色蠟黃得像張紙,嘴唇卻紅得嚇人,像是涂了胭脂。歐陽上機掀開床簾,見床頭掛著個紅布包,里面露出幾根黃黑的虎須,那虎須上還沾著些泥土。
“這是誰掛的?” 他沉聲問,聲音里帶著不易察覺的怒氣。
王屠戶的母親顫巍巍地從門后走出來,手里還攥著串佛珠,“是張婆子讓掛的,說能保母子平安,還說這虎須是她從山里老獵戶那求來的,靈驗得很。”
歐陽上機取下紅布包,往地上一摔。“啪” 的一聲,虎須落地的瞬間,產婦突然咳出一口黑血,那血落在白色的被褥上,像綻開一朵詭異的花。她眼睛緩緩睜開,眼神渙散,卻帶著股說不出的怨毒。“快,取三年的陳艾來,再燒三炷檀香。” 他一邊吩咐,一邊從懷中掏出張黃紙,咬破指尖在紙上畫了道符,那符的紋路扭曲,像是在流動。
符紙燃盡時,灰燼飄在空中,久久不散。產婦的呼吸漸漸平穩,臉色也緩和了些。歐陽上機擦了擦指尖的血:“張婆子懂些皮毛卻亂用,這虎須與產婦八字相沖,又恰逢子午相沖之日掛上,再晚半日,神仙也難救。” 他頓了頓,“把那虎須燒了,灰燼埋在院外的柳樹下,可解此劫。”
王屠戶撲通一聲跪下,磕得頭破血流,額頭很快起了個血包。“多謝先生救命之恩!多謝先生!” 歐陽上機扶起他:“起來吧,以后遇事多思量,別輕信旁人。這育兒之事,更要謹慎,不可聽信偏方。”
回到自己的小院子時,天已擦黑。夕陽的余暉從西邊的山坳里鉆出來,給院子里的老槐樹鍍上一層金邊。歐陽上機剛推開院門,就見一個黑影站在院里的老槐樹下,那影子被夕陽拉得老長,像個張牙舞爪的鬼魅。他心頭一緊,握緊了袖中的銅錢,指節因為用力而發白。
“歐陽先生別來無恙?” 黑影轉過身,聲音嘶啞得像砂紙摩擦木頭,刺耳得很。月光從云縫里鉆出來,照在他臉上 —— 竟是個沒有鼻子的怪人,兩個黑洞洞的鼻孔對著歐陽上機,邊緣還泛著暗紅,看著格外瘆人。
歐陽上機后退一步,袖中的羅盤上的指針瘋狂轉動,像是得了驚風,“閣下是誰?深夜到訪有何目的?”

怪人從懷里掏出個油紙包,扔在地上。油紙散開,露出半塊發霉的饅頭,饅頭上長著綠毛,看著讓人作嘔。“在下是黑風嶺的吳三,想請先生去看場喪事。”
黑風嶺?歐陽上機心中一驚。那地方在青溪鎮西南方,十年前就沒人住了,據說鬧鬼鬧得厲害,有樵夫說曾在夜里看到過穿白衣服的影子在嶺上飄,還聽到過哭聲。“吳當家的,我只是個算命先生,辦不了喪事。”
吳三嘿嘿一笑,露出黃黑的牙齒,牙縫里還塞著些污垢:“先生若是不去,這青溪鎮怕是要出事了。” 他說罷,身子一晃,化作一陣黑煙,“嗖” 地一下消失了,只留下一股腥臭味。
地上的發霉饅頭突然滲出鮮血,在月光下像條小蛇般蠕動,緩緩爬向歐陽上機的腳邊。歐陽上機盯著那饅頭,眉頭擰成了疙瘩。這吳三絕非善類,他口中的喪事,怕是不簡單,說不定藏著什么陰謀。
次日一早,歐陽上機正準備去鎮上打聽黑風嶺的事,剛推開院門,就見趙德發慌慌張張地跑來,他那張平日里油光滿面的臉此刻沒了血色,嘴唇哆嗦著,像是見了鬼。“歐陽先生,不好了!我那遷墳的事,怕是真惹禍了!”
原來趙德發沒聽歐陽上機的勸告,昨天趁著夜色偷偷派人去動了祖墳。今早那些人回來后,個個神志不清,胡言亂語,有個家丁還掉進河里淹死了,撈上來時臉都白了,像是被什么東西拽下去的。
“我就說壬山丙向今年犯太歲,動不得。” 歐陽上機嘆了口氣,語氣里帶著幾分無奈,“趙老板,你這是把禍水引到自己家了。太歲頭上動土,本就兇險,你還選在子時動土,那更是火上澆油。”
趙德發癱坐在地上,雙手拍著大腿,哭喪著臉:“先生,您一定要救救我啊!我趙家就指望我傳宗接代了!要是真出了什么事,我可怎么對得起列祖列宗啊!”
歐陽上機沉吟片刻。趙德發雖然固執,但罪不至死,而且這事若是處理不好,怕是會牽連到鎮上其他人。“罷了,我隨你去看看。” 他取了羅盤和桃木劍,那桃木劍是他祖父留下的,劍身上刻著細密的符文,“不過丑話說在前頭,若是真沖撞了太歲,煞氣入體,我也未必能保全你。”

兩人趕到趙家祖墳時,遠遠就聞到一股腥臭味,像是死了很久的動物。只見十幾個家丁躺在地上,口吐白沫,渾身抽搐,手腳扭曲成奇怪的姿勢。墳地周圍的草木都枯黃了,像是被火燒過一般,土地裂開一道道縫,透著股死氣。
歐陽上機拿出羅盤,指針指向墳頭,劇烈晃動,幾乎要從盤上跳下來。“果然是沖了太歲。” 他眉頭緊鎖,蹲下身摸了摸地上的土,那土冰涼刺骨,“這墳地原本是塊吉地,前有照后有靠,可惜今年太歲在壬山,你們動土時又恰逢午時,火土相沖,才招來了煞氣。你看這草,都被煞氣侵得枯了。”
趙德發聽得瑟瑟發抖,雙腿抖得像篩糠:“那…… 那現在怎么辦?先生您快想想法子啊!”
“只能暫時用符紙鎮壓,等過了今年太歲方位移了,再重新安葬。” 歐陽上機從懷中掏出幾張黃紙,用朱砂在上面畫了符,然后在墳頭四周貼上,“記住,這期間不可再靠近墳地,更不能讓孕婦和小孩過來,否則煞氣入體,神仙難救。”
正說著,遠處傳來一陣哭聲,那哭聲凄厲,聽得人心里發毛。一個老婦人跌跌撞撞地跑來,懷里抱著個草席,里面裹著掉進河里淹死的家丁尸體。她撲到尸體旁,哭得撕心裂肺:“我的兒啊!你怎么就這么去了啊!你讓娘怎么活啊!”
歐陽上機看著這場景,心中不是滋味。他轉身對趙德發說:“這煞氣已傷了人命,怕是沒那么容易鎮壓。你最好在家中供奉太歲神像,日夜上香,或許能躲過一劫。另外,給這死去的家丁好好安葬,多燒些紙錢,也算積點陰德。”
趙德發連連點頭,趕緊讓人去準備。歐陽上機看著趙家祖墳的方向,總覺得這事沒那么簡單。那煞氣來得太兇,不像是普通的沖撞太歲,倒像是有人在暗中操控,故意引煞氣出來。
他正思索著,突然看到墳地角落里有個黑影一閃而過,速度極快,像只貍貓。“誰?” 歐陽上機大喝一聲,拔腿追了過去。
黑影跑得飛快,轉眼就鉆進了旁邊的樹林里。歐陽上機追到樹林邊,只見地上有個黑色的布偶,那布偶用粗麻布縫制,上面插著七根銀針,分別扎在眼、心、手、腳的位置,布偶的胸口還用朱砂寫著趙德發的名字。
“是魘鎮之術。” 歐陽上機拿起布偶,臉色凝重。這魘鎮之術陰狠毒辣,非一般人所能為,看來有人不僅想害趙德發,還想借太歲煞氣制造事端。

歐陽上機握著那布偶,指腹摩挲著上面冰冷的銀針,心中疑竇叢生。這魘鎮之術手法詭異,針腳細密,不像是尋常山野術士所為。會是誰要害趙德發呢?難道與黑風嶺的吳三有關?他望著黑風嶺的方向,那里云霧繚繞,像是罩著一層厚厚的紗,隱約能看到山尖的輪廓,卻看不清里面藏著什么。這一切,都與吳三所說的那場喪事有關嗎?那喪事的背后,又藏著怎樣的陰謀?
歐陽上機回到鎮上,將布偶交給趙德發,告訴他有人用魘鎮之術害他。趙德發看著那布偶,嚇得臉都白了,手一抖,布偶掉在地上。他趕緊撿起來,像是拿著塊燙手的山芋:“先生,這…… 這可怎么辦啊?是誰這么歹毒,要置我于死地?”
歐陽上機將布偶放在桌上,仔細觀察著:“這布偶上的針用的是黑狗血浸過的,上面還纏著發絲,看來是對趙老板你的情況很了解。” 他頓了頓,“這魘鎮之術需要施術者的精血,而且施術者與被詛咒者距離不能太遠,想必就在這青溪鎮附近。”
“那…… 那我該怎么辦?” 趙德發哭喪著臉,“我平日里也沒得罪什么人啊,誰會這么害我?”
歐陽上機沉吟片刻:“會不會與你遷墳的那塊地有關?你買地的時候,有沒有與人結怨?”
趙德發想了想,眉頭皺起:“那地是我從一個叫李四的人手里買的,他說那是他家祖上的墳地,因為家道中落才賣的。當時他討價還價,我沒答應,還吵了幾句,難道是他?”
“不好說。” 歐陽上機搖搖頭,“李四只是個普通農戶,未必會這魘鎮之術。當務之急是找到吳三,問清楚黑風嶺的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,說不定能找到線索。”
兩人正說著,門外突然傳來一陣敲門聲,那敲門聲急促而雜亂,像是有人用拳頭在砸。開門一看,竟是個渾身是血的道士,他道袍被劃破了好幾處,臉上還有一道深可見骨的傷口,正往外滲著血。“歐陽先生,救命啊!” 道士虛弱地說,話音剛落,就晃了晃,差點栽倒。
歐陽上機趕緊將他扶進屋,讓趙德發取來傷藥和布條。“道長,發生了什么事?” 他一邊給道士包扎傷口,一邊問道。

道士喘了口氣,胸口起伏不定,像是跑了很遠的路:“我是黑風嶺的守山人,姓劉。昨天夜里,黑風嶺來了一群黑衣人,個個蒙著臉,說是要在山神廟辦喪事,還把我們這些守山人都打了一頓。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來,他們說要是找不到歐陽先生,就把整個青溪鎮都燒了!”
歐陽上機心中一凜:“他們辦的是誰的喪事?可有說是什么時候?”
“不知道。” 劉道士搖搖頭,眼神里滿是恐懼,“他們神神秘秘的,只說要請您去主持大局,還說您要是不去,后果自負。那些人手里都拿著刀,看著就不是善茬,其中一個領頭的,好像沒有鼻子……”
“沒有鼻子?” 歐陽上機和趙德發對視一眼,看來真是吳三那幫人。
趙德發在一旁聽得瑟瑟發抖,牙齒都在打顫:“先生,這可怎么辦啊?咱們還是快跑吧!跑到鄰縣去,他們找不到咱們,說不定就罷休了。”
歐陽上機瞪了他一眼:“跑?往哪跑?他們既然能找到這里,就有辦法找到鄰縣。再說,我們跑了,鎮上的百姓怎么辦?他們要是真放火燒鎮,那得多少人遭殃?事到如今,只能去會會他們了。”
他轉頭對劉道士說:“道長,你可知他們的具體位置?除了山神廟,還有沒有別的據點?”
劉道士指了指黑風嶺的方向:“就在黑風嶺的山神廟里,他們把那里圍得水泄不通,還在廟周圍挖了溝,像是在防備什么。”
歐陽上機點點頭:“好,我隨你去。趙老板,你在家中好生待著,看好結界,不要出去,也別讓外人進來。若是我三天后沒回來,你就帶著鎮上的百姓往東邊逃,那里有個廢棄的堡壘,能抵擋一陣。”
趙德發連忙點頭答應,臉上滿是感激。歐陽上機取了桃木劍和羅盤,又在懷里揣了幾張符紙和一小瓶朱砂,跟著劉道士往黑風嶺而去。

一路上,陰風陣陣,吹得樹葉沙沙作響,像是有人在暗處竊竊私語。路邊的野草長得很高,沒過了膝蓋,草葉上還掛著晨露,沾在褲腿上,冰涼刺骨。歐陽上機握緊桃木劍,警惕地觀察著四周,他總覺得有雙眼睛在盯著他們,讓人渾身不自在。
快到山神廟時,劉道士突然停住腳步,臉色煞白,嘴唇哆嗦著:“先生,我…… 我不敢進去了。那廟門口站著兩個黑衣人,手里的刀亮得嚇人,我怕……”
歐陽上機拍了拍他的肩膀,語氣沉穩:“別怕,有我在。你在這里等著,若是我半個時辰沒出來,你就回鎮上報信,讓趙老板帶人來接應。”
劉道士點點頭,躲到一棵大樹后面,探出半個腦袋看著。歐陽上機深吸一口氣,推開廟門。
廟內燈火通明,十幾支火把插在墻上,把整個大殿照得如同白晝。十幾個黑衣人站在兩旁,個個面無表情,手里握著刀,刀刃上還沾著血跡。大殿中間放著一口棺材,那棺材是黑色的,上面雕著些詭異的花紋,看著不像尋常人家的棺木。
一個身材高大的黑衣人轉過身,正是吳三。他臉上的黑洞對著歐陽上機,嘴角咧開一個詭異的笑容:“歐陽先生,你可算來了。”
歐陽上機沒動,目光落在那口棺材上:“棺材里是誰?你們到底想干什么?”
吳三指了指棺材:“這里面是我們當家的,他前幾日去世了,想請先生來看看下葬的日子和方位,務必選個風水寶地,讓他在陰間也能享福。”
歐陽上機冷笑一聲:“用得著這么興師動眾嗎?還傷及無辜,連守山人都不放過。我看你們不是想辦喪事,是想借喪事做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吧。”
“沒辦法。” 吳三聳聳肩,語氣里帶著一絲得意,“我們當家的生前最信這些,要是辦不好,我們都得遭殃。先生還是乖乖聽話,不然這青溪鎮的百姓……”
歐陽上機走到棺材前,伸出手想摸一摸,卻被吳三攔住。“先生還是先算算吧,別碰壞了我們當家的遺體,他生前脾氣可不好。”

歐陽上機皺了皺眉,從袖中取出羅盤。羅盤的指針指向棺材,瘋狂轉動,比在趙家祖墳時還要劇烈,幾乎要掙脫出來。“這棺材有問題。” 他沉聲道,“里面的東西,絕非善類。”
吳三臉色一變:“先生什么意思?難道懷疑我們當家的不是人?”
“這里面的人,死得不正常。” 歐陽上機盯著棺材,目光銳利,“而且這山神廟的方位,今年正好犯太歲,處于壬山丙向,若是在這里下葬,不出三日,煞氣必溢,整個黑風嶺都會被煞氣籠罩,到時候別說青溪鎮,就是方圓百里,都要遭殃。”
吳三哈哈一笑,笑聲里帶著股邪氣:“先生多慮了,我們當家的生前就說過,要葬在這山神廟里,說這里是風水寶地,能保佑我們兄弟發財。”
歐陽上機搖搖頭:“冥頑不靈。這‘太歲壓祭主’的忌諱你們沒聽過嗎?祭主本是逝者,若葬在太歲方位,便是主被壓,煞氣反噬,不出百日,你們這些參與喪事的人,都會損運招災,重則丟了性命,輕則斷手斷腳,一生坎坷。”
吳三臉色陰沉下來,眼中閃過一絲狠厲:“先生是在嚇唬我們?”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 歐陽上機收起羅盤,轉身就要走,“我言盡于此,告辭。”
他剛走到門口,就被兩個黑衣人攔住。“先生既然來了,就別想走了。” 吳三冷笑道,“要么幫我們辦好喪事,選個好日子,要么就留在這里陪我們當家的,也讓你嘗嘗被太歲壓著的滋味。”
歐陽上機握緊桃木劍:“你們以為能攔得住我?”
“那就試試。” 吳三一聲令下,黑衣人紛紛拔出刀,向歐陽上機撲來。
歐陽上機不慌不忙,掏出幾張符紙,往空中一撒,同時口中念念有詞。符紙瞬間燃起,化作一道道火墻,將黑衣人擋住。火墻溫度極高,烤得黑衣人連連后退。他趁機跳出廟門,往青溪鎮跑去。
身后傳來吳三的怒吼:“追!給我追!不能讓他跑了!”
歐陽上機一路狂奔,身后的腳步聲越來越近。他知道不能直接回鎮上,否則會把黑衣人引過去。于是他拐進一條小路,往旁邊的山谷跑去。

跑到山谷深處,他見旁邊有個山洞,便閃身躲了進去。剛藏好,就聽到黑衣人追了過來,他們在洞口徘徊了一陣,罵罵咧咧地走了。
歐陽上機松了口氣,靠在洞壁上休息。他看著洞外的天色,已是黃昏,夕陽的余暉透過樹葉灑進來,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。他知道,這事還沒完,吳三他們絕不會善罷甘休。
過了約莫一個時辰,估摸著黑衣人走遠了,歐陽上機才從山洞里出來,往青溪鎮走去。回到鎮上時,天已全黑,鎮上家家戶戶都關了門,街道上空無一人,只有幾盞燈籠在風中搖曳,透著股蕭瑟。
歐陽上機立刻找到趙德發,告訴他黑風嶺的情況。“那些人是一群亡命之徒,還想強行在太歲方位下葬,恐怕會給青溪鎮帶來災難。我們得想辦法阻止他們。”
趙德發急得團團轉,雙手背在身后,在屋里來回踱步:“那怎么辦啊?我們要不要報官?讓官府派兵來剿了他們。”
“報官怕是沒用。” 歐陽上機搖搖頭,“那些人行蹤詭秘,黑風嶺地形復雜,官府未必能抓到他們。而且他們手里有人命,被逼急了,說不定真會做出放火燒鎮的事來。看來只能想辦法阻止他們下葬了。”
兩人正商量著,突然聽到外面傳來一陣喧嘩,還有人喊著 “著火了”。他們趕緊跑到門口一看,只見鎮口火光沖天,映紅了半邊天。一群村民抬著擔架,慌慌張張地跑來,上面躺著幾個受傷的人,身上都有刀傷。“是黑風嶺的人!” 有人大喊,“他們來報復了!”
原來黑風嶺的黑衣人見歐陽上機跑了,竟惱羞成怒,跑到青溪鎮來鬧事,不僅放了火,還打傷了好幾個村民。歐陽上機怒火中燒:“這些人太囂張了!簡直無法無天!”
他拿起桃木劍,對圍過來的村民們說:“大家跟我走,去會會他們!不能讓他們在咱們鎮上撒野!”
村民們群情激憤,紛紛回家拿起鋤頭、扁擔、菜刀,跟著歐陽上機往鎮口跑去。只見十幾個黑衣人正在鎮口燒殺搶掠,他們砍倒了鎮口的牌坊,還在幾家店鋪門口放了火,濃煙滾滾,嗆得人睜不開眼。

“住手!” 歐陽上機大喝一聲,沖了上去。他揮舞著桃木劍,劍身上的符文在火光中閃爍。一個黑衣人舉刀向他砍來,歐陽上機側身躲過,同時一劍刺向黑衣人的手腕,那黑衣人慘叫一聲,刀掉在地上。
村民們也紛紛上前,與黑衣人搏斗。雖然村民們沒什么武藝,但人多勢眾,又抱著保衛家園的決心,打得黑衣人連連后退。
歐陽上機的劍術精湛,加上符紙的相助,很快就打倒了幾個黑衣人。吳三見狀,親自提刀沖了上來。他的刀又寬又大,劈下來時帶著風聲,力道十足。
兩人你來我往,打得難解難分。吳三的刀法狠辣,招招致命,歐陽上機則身法靈活,避實就虛,桃木劍專刺黑衣人的破綻。
打著打著,歐陽上機突然發現吳三的招式有些眼熟,他的步法詭異,出刀時總愛先跺一下腳,像是在催動什么。他心念一動,想起祖父留下的《宅經》里記載過一種邪術,叫陰煞功,練這種邪術的人動作就與吳三相似,而且身上會有股腥臭味。
“你練的是陰煞功?” 歐陽上機大喝一聲,一劍逼退吳三。
吳三臉色一變,眼中閃過一絲驚訝: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果然如此。” 歐陽上機冷笑一聲,“這種邪術傷天害理,練到最后只會走火入魔,不得好死。你為了練這邪術,怕是害了不少人吧。”
吳三被說中痛處,變得更加瘋狂:“我不好過,你也別想好過!” 他使出全力,一刀向歐陽上機砍來,刀身上泛起一層黑氣,那黑氣中帶著股腥臭味,讓人作嘔。
歐陽上機早有準備,側身躲過,同時將一張符紙貼在吳三身上。那符紙是用朱砂混合公雞血畫成的,專克陰邪。符紙貼在吳三身上,瞬間燃起,藍色的火焰舔舐著他的衣服。

吳三慘叫一聲,倒在地上,渾身抽搐,身上的黑氣被火焰燒得滋滋作響,漸漸消散。他指著歐陽上機,想說什么,卻只發出嗬嗬的怪響,最后頭一歪,沒了氣息。
其他黑衣人見頭目被打倒,都嚇得四散奔逃。村民們紛紛追趕,將他們一網打盡,捆了起來。
歐陽上機走到吳三的尸體旁,檢查了一下,確認他已經死了。他抬頭望向黑風嶺的方向,對村民們說:“我們得去黑風嶺的山神廟看看,把那口棺材處理掉,否則煞氣擴散,后果不堪設想。”
村民們雖然有些害怕,但在歐陽上機的帶領下,還是鼓起勇氣,跟著他往黑風嶺走去。
到了山神廟,只見里面空無一人,只有那口棺材還放在大殿中間。歐陽上機讓人找來斧頭,小心翼翼地將棺材蓋撬開。
棺材里躺著的不是什么大當家,而是一個稻草人,那稻草人用粗麻繩捆著,身上貼滿了符咒,符咒上的字跡扭曲,像是用血寫的。稻草人的頭頂還戴著一頂黑色的帽子,看著詭異得很。
“果然是個騙局。” 歐陽上機恍然大悟,“他們是想用這稻草人來吸收太歲的煞氣,修煉陰煞功。這稻草人身上的符咒是引煞符,能將周圍的煞氣都吸到身上,然后被施術者吸收。”
他讓人把稻草人抬出來,一把火燒了。火焰中,稻草人發出噼啪的響聲,還冒出一股黑煙,那黑煙在空中扭曲,像是在掙扎,最后漸漸散去。
歐陽上機又在山神廟里布下結界,用符咒將四周的煞氣鎖住,防止煞氣擴散。做完這一切,他才松了口氣。
回到青溪鎮,已是第二天清晨。村民們都對歐陽上機感激不盡,紛紛送來禮物,有送米的,有送面的,還有送布的。歐陽上機婉言謝絕:“保護大家是應該的,不用這么客氣。大家還是趕緊收拾鎮子,把受傷的人好好醫治,把燒壞的房子修一修吧。”
趙德發也過來道歉,他手里捧著個錦盒,里面裝著一錠銀子:“先生,之前是我不好,不聽您的勸告,差點惹了大禍。這錠銀子您收下,算是我的一點心意。”
歐陽上機擺擺手:“過去的事就別提了,以后遇事多注意些就好。這銀子你還是留著,給鎮上受傷的村民治傷吧。”
趙德發見他執意不收,只好作罷,心中對歐陽上機更加敬佩。

這場由喪事禁忌引發的風波總算平息。歐陽上機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氣,不僅阻止了一場災難,也讓村民們明白了玄學禁忌并非空穴來風。太歲壓祭主,喪事有法則,這些古老的傳承蘊含著古人對天地自然的敬畏,也藏著對生命的尊重。
在生活中,我們或許不必過度迷信,但對傳統文化應心懷尊重。那些流傳下來的禁忌,往往是前人經驗的總結,是對自然規律的順應。行事多一分謹慎,多一分敬畏,方能趨吉避兇,安穩度日。
而歐陽上機的故事,也在青溪鎮流傳開來,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。每當有人家遇到紅白喜事,總會想起歐陽先生的話,謹慎行事。而那棵老槐樹下的小院,依舊安靜地立在鎮東頭,等待著下一個需要指引的人,也見證著青溪鎮的平安與祥和。敬畏自然,遵守規律,這或許就是古人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