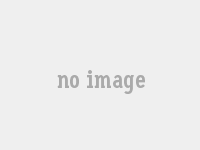姨媽借住4年賴著不走,我賣房搬遷,次日她哭暈在街頭!
“你這個白眼狼!沒良心的東西!我辛辛苦苦幫你帶孩子,現(xiàn)在翅膀硬了就要趕我走?我告訴你,這房子我住了四年,就是我的家!你敢動我一下試試!”姨媽張桂芬像一堵墻,死死堵在臥室門口,雙手叉腰,唾沫星子噴了沈月一臉。
“姨媽,這房子我已經(jīng)賣了,咱們早就說好的……”沈月攥緊了手里的行李箱拉桿,指節(jié)因用力而泛白。
“我不管!賣了也得給我住!不然我就死在這兒!”姨媽一屁股坐到地上,開始拍著大腿嚎啕大哭,“我的命怎么這么苦啊!養(yǎng)出個狼心狗肺的親戚啊!快來看啊,外甥女發(fā)達了,就要把我這把老骨頭趕出家門,不給我活路啦!”
丈夫方宇一臉為難,扯著沈月的衣袖,壓低聲音:“老婆,要不……再緩緩?你看姨媽都這樣了,傳出去不好聽。”
“不能緩!”沈月盯著地上撒潑打滾的姨媽,心臟一寸寸變冷,也一寸寸變硬。這四年的忍耐,在這一刻悉數(shù)化為堅冰。
就在這時,“咚咚咚”,急促的敲門聲像重錘敲在每個人的心上。方宇如蒙大赦,趕緊跑去開門。
門口站著兩個西裝革履的男人,神情嚴肅,其中一人推了推眼鏡,目光掃過屋內(nèi)的一片狼藉,最后落在沈月身上,語氣不帶絲毫感情地開口:“你好,沈女士嗎?我們是新房主,按照合同,今天是交房的最后期限。我們的搬家公司,已經(jīng)在樓下了。”
01
四年前的那個夏天,蟬鳴聒噪,空氣里都是粘稠的熱氣。姨媽張桂芬就是在那樣的天氣里,帶著兩個巨大的蛇皮袋和一臉“我為你犧牲了全世界”的悲壯表情,按響了沈月家的門鈴。
開門前,沈月正在廚房里,小心翼翼地把一盒打折的排骨分成三份,用保鮮袋裝好,準備吃上一個星期。她和丈夫方宇,正處在婚姻里最需要“精打細算”的階段。
他們住在單位分的二居室里,面積不大,但地段不錯。兩人最大的夢想,就是攢夠首付,在兒子睿睿上小學(xué)前,換一個帶學(xué)區(qū)的三居室。為了這個夢想,他們的生活被壓縮成了一張精準的收支表。
方宇戒了煙,每天的交通工具從地鐵換成了騎四十分鐘共享單車。沈月則剪掉了長發(fā),省下了每年上千塊的燙染護理費,化妝臺上的瓶瓶罐罐被清一色換成了國產(chǎn)基礎(chǔ)款,超過兩百塊的衣服,她連試穿的勇氣都沒有。兩人中午都帶飯,晚飯經(jīng)常是面條配青菜,唯一的娛樂是周末去免費的公園散步。
每一分錢,都掰成兩半花。銀行卡里緩慢增長的數(shù)字,是他們對抗生活壓力的唯一底氣。
姨媽的到來,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。
她是方宇母親的親妹妹,一個典型的農(nóng)村婦女,嗓門大,心思活絡(luò),尤其擅長哭窮和道德綁架。她來的理由冠冕堂皇——她唯一的兒子要結(jié)婚,女方要求必須用老兩口的房子當婚房,他們老兩口沒地方去,想來城里“暫住”幾個月,等兒子婚禮辦完,在附近租個小房子就搬走。
電話里,姨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:“小宇啊,你可是我從小看到大的,小時候你媽忙,我還給你喂過奶呢!現(xiàn)在姨媽遇到難處了,你可不能不管我啊!就幾個月,姨媽給你們做飯,幫你們看家,絕不添亂!”
方宇心軟了。他從小確實和姨媽家走得近,覺得親戚有難,伸手拉一把是天經(jīng)地義。沈月雖然心里有些嘀咕,但看著丈夫為難的樣子,又想到家里確實空著一間次臥,便也點了頭。她當時天真地想,多個長輩在,或許家里還能熱鬧些。
可她萬萬沒想到,這不是請來了一位親戚,而是引來了一尊“活菩薩”。
姨媽剛來的第一天,就展現(xiàn)出了驚人的“反客為主”能力。她帶來的兩個蛇皮袋里,塞滿了她的舊衣服、床單被罩,甚至還有一個掉漆的搪瓷盆。她毫不客氣地把沈月放在次臥里的書桌和瑜伽墊堆到角落,把自己的東西攤了一床一地,仿佛這里才是她的主場。
飯桌上,沈月特意多做了一個菜,那盒舍不得吃的排骨也燉了。結(jié)果姨媽一個人就承包了半盤,一邊吃得滿嘴流油,一邊點評:“小月啊,你這排骨買得不好,肉太柴了。下次買菜叫上我,我?guī)湍闾簦视趾糜直阋恕!?/span>
沈月尷尬地笑了笑,沒說話。
接下來的日子,才是噩夢的真正開始。
姨媽完美地詮釋了什么叫“耗電費水第一名,省錢說教第一名”。她洗澡能洗一個小時,水聲嘩嘩的,讓沈月的心跟著滴血;夏天開空調(diào),她總要把溫度調(diào)到最低,自己裹著被子,還振振有詞:“人老了,怕熱,中暑了看病更花錢。”可一轉(zhuǎn)身,她看到沈月給手機充電超過三小時,就會立刻拔掉,痛心疾首地說:“哎喲,電費不要錢啊?你們年輕人就是不知道節(jié)省!”
沈月買的進口水果,她總能第一時間找到,一顆不剩地吃完,然后擦擦嘴說:“這洋玩意兒也沒什么好吃的,還不如我們家鄉(xiāng)的土蘋果。”沈月新買的一瓶三百多的精華液,沒用幾次就見了底,后來才發(fā)現(xiàn)是被姨媽拿去抹腳后跟了,理由是“我看這瓶子挺好看,想著里面的東西肯定能治我的腳干裂”。
這些都還只是生活習(xí)慣的摩擦,真正讓沈免月感到窒息的,是精神上的侵蝕。姨媽像一個移動的監(jiān)控,監(jiān)視著家里的一切。她會翻看小兩口的購物賬單,對每一筆“不必要”的開銷指指點點;她會偷聽他們夫妻倆在臥室里的談話,第二天在飯桌上意有所指地敲打。
最讓沈月無法忍受的,是她對兒子睿睿的“關(guān)心”。
睿睿當時剛一歲多,沈月堅持科學(xué)喂養(yǎng)。可姨媽總有自己的一套“老理兒”。她會把飯菜自己嚼爛了再喂給睿睿,沈月阻止她,她就哭天搶地:“我兒子就是這么喂大的,長得多壯實!你們讀了幾天書,就嫌棄我們老的臟?我這是疼孩子,你當媽的倒好,一點不領(lǐng)情!”
她還喜歡給睿睿穿得里三層外三層,哪怕是夏天,也要捂出滿身的痱子,美其名曰“小孩兒沒有六月天,不能著涼”。
每一次爭執(zhí),方宇都扮演著和事佬的角色。“老婆,她也是好心,她一個長輩,你跟她計較什么?”“她是我姨媽,我總不能趕她走吧?忍一忍,就幾個月。”
“幾個月”成了一個遙遙無期的承諾。
姨媽兒子的婚禮辦完了,她說要等兒媳婦懷孕,幫著照顧月子。兒媳婦生了,她說孩子太小離不開人,得等孩子上幼兒園。幼兒園上了,她又說自己身體不好,渾身是病,需要在大城市看病調(diào)養(yǎng)。
理由一個接一個,每一個都充滿了無法辯駁的“親情”與“道義”。四年時間,就這樣在無休止的忍耐和退讓中流逝了。那間次臥,徹底成了姨媽的領(lǐng)地。而沈月和方宇的“三居室夢”,也被無限期擱置。
02
壓死駱駝的,從來不是最后一根稻草,而是日積月累的每一根。
四年的時間,足以改變很多事情。沈月的兒子睿睿從一個牙牙學(xué)語的嬰兒,長成了一個活潑好動的小男孩。原本還算寬敞的二居室,隨著孩子的長大,變得越來越擁擠。睿睿的玩具、繪本、小衣服,幾乎占據(jù)了客廳的半壁江山。
而姨媽的存在,則讓這種擁擠感從物理空間蔓延到了心理空間。
每天下班回家,沈月推開門的瞬間,聽到的不是兒子的歡聲笑語,而是姨媽在客廳里開著最大音量追的婆媳倫理劇,和她那中氣十足的點評聲。飯桌上,最好的菜永遠在姨媽面前,她會一邊剔著牙,一邊數(shù)落沈月工作忙,不管家,不像個女人。
晚上,睿睿偶爾哭鬧,姨媽就會在自己房間里大聲咳嗽,或者故意把門摔得震天響,無聲地抗議著“噪音”。小兩口想親熱一下,都得豎起耳朵聽隔壁的動靜,生怕被姨媽撞見,那種感覺比做賊還心虛。
沈月感覺自己像一個寄居在自己家里的客人。她越來越沉默,臉上的笑容也越來越少。她開始失眠,夜里常常睜著眼睛,聽著隔壁姨媽響亮的鼾聲和丈夫均勻的呼吸聲,感到一種深入骨髓的孤獨和絕望。
她和方宇的爭吵也多了起來。
“方宇,我們什么時候才能有自己的生活?”一次,沈月在陽臺上,看著遠處亮燈的萬家燈火,聲音里帶著哭腔。
“老婆,再忍忍,姨媽年紀大了,身體又不好……”方宇的回答永遠是這一句。
“她身體不好?她每天去樓下跳廣場舞,比誰都有勁!她去超市搶特價雞蛋,能把年輕人擠開!她哪里不好了?”沈月的情緒有些激動。
“你小聲點!被她聽見了!”方宇緊張地看了一眼客廳的方向。
就是這個動作,徹底刺痛了沈月。在這個家里,丈夫的第一反應(yīng)永遠是“別讓姨媽聽見”,而不是體諒她的委屈。她感覺自己像一個孤軍奮戰(zhàn)的士兵,背后空無一人。
真正的轉(zhuǎn)折點,發(fā)生在睿睿四歲生日那天。
沈月特意請了半天假,花三百塊錢訂了一個漂亮的汽車蛋糕,想給兒子一個驚喜。結(jié)果她回到家,發(fā)現(xiàn)蛋糕已經(jīng)被切開,吃掉了一大半。睿睿正坐在地毯上哭,臉上身上全是奶油。
姨媽則坐在沙發(fā)上,一邊用牙簽剔著牙,一邊教訓(xùn)睿睿:“哭什么哭!不就是個蛋糕嗎?我先嘗嘗有沒有毒,你媽在外面買的東西,誰知道干不干凈!再說,你一個小孩子家,過什么生日,浪費錢!”
沈月腦子里“嗡”的一聲,所有的委屈、憤怒、壓抑,在那一刻全部沖上了頭頂。她沖過去抱起兒子,看著他哭得通紅的小臉,聲音都在發(fā)抖:“姨媽!你太過分了!這是睿睿的生日蛋糕!”
“我怎么過分了?我吃塊蛋糕怎么了?你家大業(yè)大,還差我這一口?真是越有錢越小氣!”姨媽梗著脖子,毫無悔意。
那天晚上,沈月和方宇爆發(fā)了有史以來最激烈的一次爭吵。
“方宇,我受夠了!這個家,有她沒我,有我沒她!我們必須賣掉這套房子,立刻,馬上!”沈月把所有的銀行卡、房產(chǎn)證都拍在桌子上,眼睛通紅。
“老婆,你冷靜點,為了塊蛋糕,至于嗎?”
“至于嗎?”沈月笑了,笑得比哭還難看,“這不是一塊蛋糕的事!是四年!整整四年!我的家被她搞得烏煙瘴氣,我的兒子在她眼里連塊蛋糕都不配吃,我的丈夫只會讓我忍!方宇,你告訴我,這個家到底是誰的?如果今天你不做決定,那我們就離婚!”
“離婚”兩個字,像一記重錘,終于敲醒了渾渾噩噩的方宇。他看著妻子決絕的眼神,第一次感到了恐慌。他意識到,他所謂的“孝順”和“忍讓”,已經(jīng)把自己的小家庭推到了懸崖邊緣。
那一夜,夫妻倆談了很久。沈月把自己四年來的所有委屈和盤托出,那些被姨媽偷偷倒掉的母乳,那些被她剪壞的昂貴衣服,那些當著外人面對她的貶低和羞辱……樁樁件件,都像刀子一樣,扎在方宇心上。
天亮?xí)r,方宇終于下定了決心:“好,我們賣房。”
03
下定決心是一回事,執(zhí)行起來又是另一回事。
當沈月和方宇第一次向姨媽提出賣房計劃時,姨媽的反應(yīng)堪稱影后級別。她先是震驚,然后是不可置信,最后捂著胸口,眼淚說來就來。
“你們……你們這是要趕我走啊!我這把老骨頭,在這里給你們當牛做馬四年,沒有功勞也有苦勞,現(xiàn)在你們嫌我礙事了,就要把我掃地出門?我的命怎么這么苦啊!”
她一邊哭嚎,一邊給老家的親戚挨個打電話,添油加醋地控訴沈月和方宇的“不孝”。一時間,各種“勸說”電話紛至沓來,無一例外都是指責(zé)沈月不懂事,不體諒長輩,心腸太狠。
方宇的防線再一次動搖了。他夾在中間,左右為難,又開始勸沈月:“要不……我們再想想別的辦法?買個小一點的,或者租個房子?”
但這一次,沈月沒有退讓。那塊被毀掉的生日蛋糕,像一個警鐘,時刻提醒著她,退讓換不來安寧,只會讓對方變本加厲。
“沒有別的辦法。”沈月的語氣異常平靜,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堅定,“方宇,我們的目標是給睿睿一個好的成長環(huán)境,不是為了供養(yǎng)一個無理取鬧的親戚。如果你再動搖,那我們就連夫妻都沒得做了。”
沈月開始默默地行動起來。她聯(lián)系了中介,把房子掛了出去。
姨媽的“戰(zhàn)斗”也隨之升級。只要有中介帶人來看房,她就故意把家里弄得亂七八糟,垃圾堆在客廳,臟衣服扔在沙發(fā)上。客人來了,她就穿著睡衣,趿拉著拖鞋,在屋里晃來晃去,用審視的目光打量著每一個人,時不時還咳嗽兩聲,陰陽怪氣地說:“這房子風(fēng)水不好,潮得很,誰住誰倒霉。”
好幾個意向強烈的買家,都被她這副樣子嚇跑了。中介私下里跟沈月抱怨:“沈姐,你家這位長輩不走,這房子根本賣不掉啊。”
沈月的心一點點沉下去。她意識到,用常規(guī)手段,她永遠贏不了這個“撒潑耍賴”的姨媽。絕望之中,一個大膽的念頭在她腦海里成型。
她開始暗中觀察,尋找一個突破口。她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規(guī)律,姨媽每天下午三點到五點,雷打不動地要去樓下的小花園,和一群老太太聊天、跳舞。這是她一天中唯一的“社交時間”,也是家里唯一的清凈時刻。
沈月抓住這個機會,偷偷聯(lián)系了一個新的中介,要求他只在這個時間段帶客戶來看房。為了速戰(zhàn)速決,她把價格降了十萬,但提出了一個條件:買家必須能全款,并且在一個月內(nèi)完成所有交易,盡快交房。
這個條件吸引了一對急著給孩子落戶上學(xué)的年輕夫妻。他們來看房時,家里干凈整潔,陽光明媚。沈月親自接待,詳細介紹了房子的優(yōu)點和周邊的配套。夫妻倆非常滿意,當場就付了定金。
整個過程,沈月都瞞著方宇和姨媽。她知道,一旦讓他們知道,這件事肯定會節(jié)外生枝。她獨自一人去簽了合同,辦了手續(xù),拿著那份白紙黑字的合同,她的手在抖,心里卻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踏實感。
她不是在算計親人,她是在拯救自己的家。
交房的日子一天天臨近,沈月開始不動聲色地打包家里的東西。她把不常用的書籍、換季的衣物都裝進箱子,堆在臥室角落。
姨媽有所察覺,警惕地問:“小月,你這是干什么?你該不會真的把房子賣了吧?”
“收拾一下,家里太亂了。”沈月輕描淡寫地回答。
她給了姨媽最后的體面和機會。在交房日期的前一個星期,她和方宇一起,最后一次正式和姨媽談話。
“姨媽,房子已經(jīng)賣了,下周一交房。我們已經(jīng)在附近給您看好了一套一居室的出租房,租金我們先幫您付半年。您看您是搬過去,還是回老家您兒子那邊?”沈月把租房信息放在姨媽面前,語氣平靜。
姨媽盯著那份租房信息,沉默了足足一分鐘。然后,她猛地把傳單撕得粉碎,歇斯底里地爆發(fā)了。
于是,便上演了開頭那一幕。撒潑、打滾、哭嚎、謾罵,她用盡了自己四年來屢試不爽的所有招數(shù),試圖逼迫沈月再次妥協(xié)。
方宇果然又一次心軟了,他拉著沈月,想讓她“緩緩”。
但沈月只是冷冷地看著地上的姨媽,她知道,這一次,她身后沒有退路。她等的,就是那個敲門聲。那是她為自己,也為這個家,請來的“救兵”。
04
當那兩個西裝革履的男人說出“我們是新房主”時,整個客廳的空氣仿佛都凝固了。
地上嚎哭的姨媽張桂芬,哭聲戛然而止,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鴨子。她抬起頭,滿是淚痕的臉上寫滿了錯愕和不信。
方宇也愣住了,他看看門口的陌生人,又看看一臉平靜的妻子,腦子里一片空白。他知道沈月在賣房,但他不知道,一切已經(jīng)塵埃落定,甚至到了交房的最后期限。
“你們……你們是誰?胡說八道什么!”姨媽最先反應(yīng)過來,她從地上一躍而起,叉著腰,擺出了戰(zhàn)斗姿態(tài),“這是我的家!你們趕緊走,不然我報警了!”
其中一位姓李的新房主推了推眼鏡,從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,遞到姨媽面前,語氣客氣但疏離:“阿姨,您好。這是房產(chǎn)證和購房合同,法律上,這套房子從今天零點起,已經(jīng)屬于我們了。我們是合法業(yè)主,您再說這樣的話,我們也可以報警,告您私闖民宅。”
白紙黑字,紅色的印章,刺眼得讓人無法懷疑。
姨媽的囂張氣焰瞬間熄滅了一半,她難以置信地看向沈月,眼神里充滿了怨毒:“沈月!你……你竟然來陰的!你背著我們把房子賣了!”
沈月沒有理會她,而是轉(zhuǎn)向兩位新房主,歉意地笑了笑:“李先生,王先生,不好意思,家里出了點意外,給你們添麻煩了。我們馬上就清理好。”
說著,她拿起手機,撥了一個號碼:“喂,是順心搬家公司嗎?對,可以上來了,地址是……對,全部搬走。”
電話掛斷不到五分鐘,樓道里就傳來一陣嘈雜的腳步聲。四個穿著統(tǒng)一藍色工服的搬家?guī)煾担е障渥樱~貫而入。
“沈女士您好!請問先從哪個房間開始?”領(lǐng)頭的師傅聲音洪亮。
“就從這個房間開始。”沈月指了指姨媽住了四年的次臥。
這下,姨媽徹底慌了神。她像一只被侵犯了領(lǐng)地的母獅,張開雙臂死死堵在次臥門口:“我看誰敢動!這是我的房間!我的東西誰都別想碰!”
搬家?guī)煾祩兠婷嫦嘤U,停下了腳步,看向沈月。
沈月深吸一口氣,緩緩走到姨媽面前。這四年來,她第一次用一種居高臨下的、不帶任何溫度的眼神看著這位長輩。
“姨媽,”她的聲音不大,卻清晰地傳到在場每一個人的耳朵里,“我再叫您最后一聲姨媽。四年前,您說來暫住幾個月,我們信了。這四年,您吃我們家的,住我們家的,把我當保姆使喚,把我兒子當玩具折騰,把我的忍讓當成理所當然,我也忍了。”
她的目光掃過姨媽身上那件明顯是自己買給母親、卻被姨媽“借”走的名牌羊毛衫,繼續(xù)說道:“我體諒您年紀大,體諒您兒子不容易,處處為您著想。可您呢?您把我的家當成自己的,把我的善良踩在腳底下。我跟您好好商量,您撒潑打滾;我給您找好退路,您罵我白眼狼。”
“現(xiàn)在,我不想跟您講道理,也不想跟您論親情了。”沈月的聲音越來越冷,像冬日里的冰棱,“這房子,我已經(jīng)賣了。錢,在我的賬戶里。我們的新家,也已經(jīng)買好了,裝修得干干凈凈,等著我們一家三口住進去。而您,”她頓了頓,一字一句地說,“從今天起,和這個家,和我們,再也沒有任何關(guān)系。”
“把她的東西,全部打包,搬到樓下大門口。”沈月轉(zhuǎn)身對搬家?guī)煾祩兿逻_了命令,語氣果決,不容置疑。
方宇徹底看呆了。他從沒見過這樣的沈月,冷靜、強大,帶著一種令人畏懼的氣場。他心中的那點猶豫和不忍,在妻子這番話面前,顯得那么蒼白可笑。他終于明白,沈月是被逼到了何種絕境,才會變得如此“狠心”。
搬家?guī)煾祩兊玫搅嗣鞔_的指令,不再猶豫。兩個師傅上前,一左一右,客氣而強硬地將還在發(fā)愣的姨媽“請”到了一邊。另外兩個師傅則走進次臥,開始飛快地將姨媽的衣物、被褥、雜物往箱子里裝。
“啊——你們干什么!放開我!我的東西!你們這群強盜!”姨媽終于反應(yīng)過來,開始瘋狂地掙扎、尖叫。
但一切都是徒勞。她的那些寶貝——攢了半年的廢報紙,超市領(lǐng)的塑料盆,發(fā)黃的舊床單,被專業(yè)而高效地清空、打包、封箱,然后被抬了出去。
她的“王國”,在短短十幾分鐘內(nèi),土崩瓦解。
05
整個搬家過程,像一場快節(jié)奏的舞臺劇。沈月冷靜地指揮著,告訴師傅們哪些要搬走,哪些是留給新房主的。方宇則默默地抱著兒子睿睿,站在一旁,眼神復(fù)雜地看著妻子忙碌的背影。
睿睿似乎也感受到了氣氛的變化,他沒有哭鬧,只是緊緊地摟著爸爸的脖子,大眼睛好奇地看著眼前的一切。
姨媽的哭喊聲漸漸變成了絕望的哀嚎。她眼睜睜地看著自己住了四年的房間被搬空,看著那些熟悉的家具被貼上標簽,看著這個她早已視為囊中之物的“家”離她遠去。她的力氣仿佛被抽空了,癱坐在地上,眼神空洞,嘴里喃喃地重復(fù)著:“怎么會這樣……怎么會這樣……”
新房主李先生夫婦全程目睹了這一切,他們沒有催促,只是安靜地站在角落。等最后一個箱子被搬出門,李先生才走過來,對沈月說:“沈女士,我們能理解。謝謝你遵守合同。”
沈月點點頭,露出一絲疲憊的微笑:“應(yīng)該的。祝你們?nèi)胱∮淇臁!?/span>
她牽起方宇的手,抱著兒子,一家三口,最后看了一眼這個承載了他們無數(shù)喜怒哀樂和委屈的家,然后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
樓下,搬家的卡車已經(jīng)裝得滿滿當當。而在單元門口的空地上,堆著十幾個紙箱和幾個蛇皮袋,那是姨媽的全部家當。
姨媽被幾個好心的鄰居攙扶著,站在那堆東西旁邊,頭發(fā)凌亂,眼神呆滯,像一個被遺棄的流浪者。她看到沈月一家走出來,眼神里迸發(fā)出最后一點怨毒的光芒,張嘴想罵,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
沈月沒有看她,徑直走到自家的車前,打開車門,讓方宇和孩子先上去。她坐進駕駛座,發(fā)動了汽車。
車子緩緩駛離小區(qū)時,沈月從后視鏡里,看到了姨媽的身影。她追著車子跑了幾步,然后腿一軟,摔倒在地,趴在那堆屬于她的行李上,嚎啕大哭。那哭聲,再也沒有了往日的囂張和算計,只剩下純粹的凄涼和絕望。
沈月面無表情地踩下油門,將那哭聲和那個糾纏了她四年的噩夢,一同甩在了身后。
車里一片寂靜。許久,方宇才開口,聲音沙啞:“老婆,對不起。”
沈月沒有說話,只是伸出右手,緊緊地握住了他放在檔位上的手。她的手心,全是冷汗。
新家是一個寬敞明亮的三居室,陽光透過落地窗灑進來,在地板上鍍上一層溫暖的金色。睿睿有了自己的房間,里面有他喜歡的藍色墻壁和汽車造型的小床。
當晚,把兒子哄睡后,沈月和方宇坐在陽臺的藤椅上,看著窗外的城市夜景。
“我今天……是不是特別狠?”沈月輕聲問,聲音里帶著一絲不確定。
方宇搖搖頭,伸手將她攬入懷中:“不,你只是做了一個我早就該做,卻一直沒有勇氣去做決定。小月,是我太軟弱,讓你受了這么多年的委屈。謝謝你,守住了我們的家。”
沈月靠在丈夫的肩膀上,緊繃了多日的神經(jīng)終于放松下來。眼淚,無聲地滑落。那不是委屈的淚,而是釋放和解脫的淚。
0.6
第二天上午,沈月正在新廚房里,哼著歌給兒子準備午餐,久違的陽光心情讓她覺得連空氣都是甜的。這時,一個陌生的電話打了進來。
是老家一個關(guān)系比較遠的表嬸。
“小月啊!不得了啦!你姨媽出事了!”表嬸的語氣焦急萬分。
沈月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但很快鎮(zhèn)定下來:“她怎么了?”
“哎喲,你還不知道啊?昨天你們搬走后,她就在你們原來那個小區(qū)門口哭,不肯走。她兒子打電話讓她過去,她也不去,說沒臉見人。今天一早,有人發(fā)現(xiàn)她暈倒在街邊,旁邊就是她的行李,被送到醫(yī)院去了,說是急火攻心,加上沒休息好,中暑了!現(xiàn)在好多親戚都在傳,說你們把她趕出去,害得她哭暈在街頭,造孽啊!”
“哭暈在街頭”,這幾個字,像一個精心設(shè)計的劇本高潮。沈月甚至能想象出姨媽躺在地上,周圍圍著一圈指指點點的路人,那副博取同情的凄慘模樣。
若是以前,她可能會立刻感到內(nèi)疚、自責(zé),甚至?xí)R上趕去醫(yī)院。但現(xiàn)在,她的心出奇地平靜。
“表嬸,我知道了。”她淡淡地說。
“啊?你就這個反應(yīng)?那可是你姨媽啊!”表嬸顯然對她的冷淡感到不可思議。
“表嬸,”沈月打斷了她的話,語氣清晰而有力,“第一,我們沒有趕她,我們給了她一周的準備時間,還幫她找好了房子,是她自己選擇在街上哭,而不是去一個有瓦遮頭的地方。第二,她有兒子,贍養(yǎng)她是她兒子的責(zé)任,不是我們外甥和外甥媳婦的。我們?nèi)手亮x盡,照顧了她四年,已經(jīng)遠遠超出了親戚的情分。第三,我問心無愧。如果善良沒有鋒芒,那它就一文不值。我的善良,只會留給我值得的家人。”
說完,她沒有給對方反駁的機會,直接掛斷了電話,然后將那個號碼拉黑。
隨后,她做了一件事。她在家族的微信群里,發(fā)了一段長長的文字。她沒有控訴,沒有指責(zé),只是平靜地陳述了四年來發(fā)生的一切,從姨媽如何找借口賴著不走,到她如何對待睿睿,如何破壞他們賣房,最后附上了新房主愿意作證的電話,和她當初替姨媽找好的租房合同照片。
她寫道:“各位長輩,各位親戚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(jīng)。我們對姨媽,已經(jīng)盡了最大的情分和耐心。往后,我們只想過好自己的小日子。關(guān)于姨媽的任何事,請直接聯(lián)系她的兒子,我們不再參與。祝各位安好。”
發(fā)完這段話,沈月直接退出了那個充滿了道德綁?架和閑言碎語的家族群。
世界,一下子清凈了。
方宇走過來,從背后抱住她,看著她手機上的操作,輕聲說:“做得對。”
07
幾天后,方宇接到了姨媽兒子,也就是他表哥的電話。電話里,表哥的語氣充滿了疲憊和無奈。
原來,姨媽在醫(yī)院折騰了一通,沒什么大礙,出院后就被他接回了家。但從此家里就雞飛狗跳,姨媽嫌兒媳婦做的飯不好吃,嫌孫子太吵,整天在家里唉聲嘆氣,抱怨兒子沒本事,讓她在親戚面前丟盡了臉。兒媳婦也不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