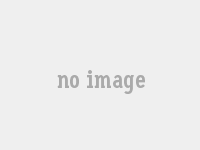4份塔城界約,傻傻分不清楚?沙俄:沒關(guān)系,都是清朝的割地條約
如果不是某次翻老地圖,我都沒在意過塔城這地方,說白了,它在大清朝時候還叫“塔爾巴哈臺”,外人一聽,還真未必曉得是哪。但是吧,塔城的小小名字,后頭卻壓著幾份讓國人咽不下氣的條約,每一份幾乎都和沙俄有千絲萬縷的關(guān)系。這不,近代史里,光是以塔城做名字、定下邊界的協(xié)議,居然給架了四份——要我說,背后可不僅是幾條線那么簡單。

你要問從哪兒開始捋?那還得倒回到19世紀(jì)中葉,清朝自己的邊防一團亂麻,沙俄那邊卻已經(jīng)把算盤打得哐哐響。剛剛簽過《北京條約》(1860年呢),還以為可以喘口氣,誰知道沙俄緊接著就抄起“邊界”的旗子,把紙筆,又往西邊的塔城遞了過來。這幫人狡猾得很,說話也挑地方,硬說只有清朝常駐的“卡倫”才能算中國的地界。卡倫,說白了,就是咱們的邊防哨站,按老清的規(guī)矩,這一哨設(shè)在哪,周圍的地盤都算它管的。沙俄呢,嘴皮子一翻:卡倫外邊的土,全是“沒主”的,能搶歸自家拉去。
話又說回來,當(dāng)年清朝并不是光靠這幾個固定卡倫,就那么守邊。咱們還有巡邏的哨子,時不時換地方,別看人不多,那是活管轄,比死板圖上多畫一條線強。可惜,這在沙俄人眼里全不算數(shù),立馬給踢開。

就這樣,1862年,沙俄眼見清廷邊防力量羸弱,干脆撂下外交辭令,一撥兵馬三萬人悄然突進,從巴爾喀什湖打到塔城、伊犁。你要說清朝那邊,除了塔城、伊犁九城勉強有點防備,其他地盤早被沙俄披荊斬棘,一路碾過去,幾乎毫無阻力。有一說一,在塔城和伊犁,這兩塊地方的清軍還真給頂了兩年,這點骨氣,算是救了點場子。
最后結(jié)局呢?還是抵不住沙俄蠻橫:倚著軍事壓力,逼著清廷談判,畫地為牢,強行把停火線變成分界線——這就是有名的《勘分西北界約記》,圈里人更多叫它《塔城議定書》。一筆筆畫過去,外西北四十四萬平方公里,整箱整箱地搬進了沙俄地界。

塔城能有這命,也怪當(dāng)時清廷一方代表明誼太實誠。他還在和俄國代表巴布科夫講道理,說要不咱們各退一步,邊線定在原始清朝邊界到雙方停火線的中間,賠出去的地,也能少一半。巴布科夫一聽,鼻子都不帶翹的,直接拂袖而去,明擺著不給任何商量余地。最后,朝中能決斷的奕?也看明白了,“不答應(yīng)以后損失更大。”一句話,塔城大片地盤就這么給寫進了條約。
只不過條約頂多是紙上談兵,真到田野間勘界立碑才麻煩得很。于是,圍著塔城又有了三道“子條約”。其中,塔城對當(dāng)?shù)啬寥撕脱策叡罹o要的,就是1870年簽訂的《塔爾巴哈臺界約》,十塊界碑落下,三十萬平方公里走了大半。剩下《科布多界約》和《烏里雅蘇臺界約》,又把科布多一線,和唐努烏梁海西北一塊地拱手送了出去。你要是此時在內(nèi)蒙古和新疆一帶趕路,天天能碰見站在上頭的俄國兵,壓根不像從前那樣歸老清家管。

可俄國人心大的很,沒完沒了。割了一塊還想再來一刀。《塔爾巴哈臺界約》剛簽完,沙俄動手又占了伊犁。一時間伊犁成了兵家必爭地,沙俄表面說是幫清朝護城,其實心里也是壘著算盤:“等你們把阿古柏收拾爽了,伊犁地盤再‘歸還’給你們。”這話讓人哭笑不得,就像借別人錢,說等我暴富再還你一樣,誰還真信?
后來左宗棠帶著兵勇氣沖天,硬把新疆收了回來。沙俄這才尷尬了:伊犁這么好的地方,真要按原話還給清廷?想賴賬又怕惹火上身,干脆弄了點招數(shù),嚇唬清朝談判官崇厚,威逼利誘,“你簽了,這地歸我,你不簽,戰(zhàn)火隨時有。”崇厚就這么稀里糊涂,自己答應(yīng)了《里瓦幾亞條約》,霍爾果斯河以西、特克斯河流域、塔城東北,全被塞進沙俄囊里。

全天下都覺得冤,哪有不打仗還割地的道理?清廷一聽,火了。但崇厚已經(jīng)成了背鍋俠,直接下獄。換了曾紀(jì)澤上陣,卻屢屢吃閉門羹。沙俄人壓根不想坐下來商量,非要你低頭。也是左宗棠夠狠,抬棺上路,一副要和沙俄死磕到底的架勢。沙俄見來真的了,才心虛敞開口子,又跟曾紀(jì)澤慢慢談。最后有了1881年《中俄伊犁條約》,勉強又收回了特克斯河流域,但霍爾果斯河以西、塔城東北七萬多平方公里還是丟了——這筆賬,到現(xiàn)在有人還在咬牙算。
往后,《中俄伊犁條約》底下一共五個“技術(shù)條款”,說是技術(shù),其實都是劃界割地的明細。其中,《科塔界約》就專門管從塔城到科布多這一段,準(zhǔn)確定了中間的幾座山頭、幾條河流,阿拉別克河以西、河口以南,都進了俄羅斯人地圖里。當(dāng)?shù)毓_克牧民就苦了,每次放牧,牛羊不敢越鐵線一步,咱們清朝自己的人也被明令不能搬進那里,更不能設(shè)哨卡,空有地皮卻做不了主。那年頭裕民縣的老人說,趕牛上山都得看人家俄國兵的臉色,委屈常常是日常。

沙俄人就是鐘情塔城,每逢邊界變動,第一件事就往這塊地方動手。后來的《塔爾巴哈臺西南界約》,還是以塔城為名字,羅列細到哈巴爾蘇到喀拉達坂之間的界碑,眼見的清朝地卻被要求限制遷民、種地,活生生地給俄國牧民騰了場子。歷史上,說到巴爾魯克山,哈薩克小伙子都能講上幾段“爺爺被趕出祖地”的故事。沙俄的無理條款,把這座山的主權(quán)掏空了,風(fēng)水輪流轉(zhuǎn),可惜等不來公道。
再一看時間線,沙俄一共圍著塔城,逼了四份條約,每次都落點不平等,把中國這頭心氣打得死死的。你說塔城有啥天大誘惑?歸根到底,是新疆北部的水草豐美、馬路通暢。從1758年起,這里就是中亞交通要道,不光商隊,也有兵家過境,釀皮子和奶茶也就在那里傳播開了。沙俄的幾任軍事外交家早就看得透:“控制塔城,盤活整個外西北。”
也難怪,自1862年沙俄吃了敗仗,打不下塔城之后,便一門心思想把這塊拿到手里。不是一次,又不是兩次,而是每逢中國局勢有變,沙俄準(zhǔn)不放過塔城地帶。一條邊界,幾份條約,背后有說不盡的心酸故事。塔城的命運,它不是紙上的名字,每條界線都是一代人心頭的哀嘆。
這么看,俄國人到底圖啥?有人說資源,有人說戰(zhàn)略,有人說對西北疆域的天然渴望。其實細想,塔城不止是一塊地,它見證了大國之間屢屢交鋒、老百姓流離失所,還有那些見風(fēng)使舵的談判桌上,誰都沒法干脆說清的隱忍。我有時翻到那張舊條約里密密麻麻的地名,腦子里就浮現(xiàn)出那年頭的冬天,城外的邊民抱著腌肉和暖炕小聲罵街:“世道真的是變了啊。”
而今天我們談塔城,討論的不只是那些丟失的平方公里,更是每一次大國談判背后的眼淚與膽氣。歷經(jīng)百年,你說現(xiàn)在的邊境是不是再不會有那種憂心?沒人能拍胸脯保證。畢竟,塔城的故事還沒講完呢。